由昆明作家协会主办的“崛起,‘昆明作家群’——陈鹏、包倬、马可、祝立根作品研讨会暨昆明文学讲堂”昨天在昆明璞玉书店顺利举办。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原云南省委副书记丹增先生,昆明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陆毅敏女士,云南省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作家李朝德先生,昆明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原滇池文学杂志主编、作家张庆国先生莅临本次活动。此次活动是针对陈鹏、包倬、马可、祝立根四位中青年作家作品的研讨,我们非常有幸请来了耿占春、张定浩、马兵和王朝军四位优秀的评论家对四位作家作品进行评论。
丹增:“昆明作家群”一定会打响,会对未来的文坛产生重大的影响
丹增书记先是回顾了云南省的三批作家群产生的文学影响,他提到在“昆明作家群”之前云南崛起过三种作家群,分别是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军旅作家群、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前后的儿童文学作家群,以及2004年崛起的昭通作家群,这三个作家群的发展与昆明作家群的出现和崛起是息息相关的。同时他提到,所谓“作家群”主要有三个概念,第一是地域,第二是人物,第三是作品。地域概念指的是在一个地域环境里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家;人物概念指的是作家群中必定会有一个或多个代表性人物;当谈及作品概念时,他重点提及了大益文学院,称赞了大益文学院推出了不少文学精品。
随后,丹增书记聊到了环境对于作家群兴起的重要性,他以昭通作家群进行举例。他认为,昆明也是一个孕育作家群的文化良地,所以昆明作家群的崛起具备良好的环境因素。
此外,他也谈到在“现代病”越发严重的当下,文学对于我们的重要作用。他相信这个由陈鹏主席亲自策划的“昆明作家群”一定会打响,会对未来的文坛产生重大的影响。
陆毅敏:文学事业是一场接力赛
陆毅敏主席首先对到场的嘉宾和昆明文学界的各位朋友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她指出近年来昆明文学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昆明老中青作家都勤奋耕耘、潜心创作,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对于这次研讨会被研讨的四位青年作家,她表达了诚挚的祝贺和深深的敬意。陆主席表示:“文学事业是一场接力赛,优秀的文学人才是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坚实支撑,培养造就一支优秀的青年作家队伍,是提升文学人才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青年是社会中最开放、最活跃、最积极的群体。青年作家是作家群体中最有艺术追求、最具创新意识、最富创造活力的文学力量。青年作家是文学的未来和希望。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为文学界创造新繁荣、书写新辉煌创造了难得的契机,为青年作家攀登艺术高峰、实现文学理想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文学事业发展也迎来了新的黄金时代。”
李朝德:让文学回归文学本身,让作者与读者实现无缝对接
在讲话开始,李朝德就表示在璞玉书店这样一个具有书卷气的地方召开这样一场研讨会,意义非凡,“这是让文学回归文学本身,让作者与读者实现无缝对接”。随后,他指出昆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与之相匹配的是文学,昆明文学也源远流长。昆明作家是云南作家中最为重要的力量,一大批作家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写下过灿烂华美的篇章,无论是小说、诗歌、散文、儿童文学、报告文学,都取得过非常巨大的成就。对于昆明文学的发展,昆明市文联、昆明作家协会、《滇池》杂志社、大益文学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代表省作家协会对昆明市文联、昆明作家协会、滇池杂志社,还有大益文学院多年来的坚持与热忱表示敬意。对于四位作家,他认为他们是昆明文学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云南文学发展的期望,他们代表着文学继往开来、勇攀高峰的文学力量,也昭示着青年作家锦绣灿烂、欣欣向荣的美好愿景。
张庆国:昆明文学不是要做云南最好的,而是要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力量
张庆国在丹增书记对云南文学四个作家群解释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深入解析,他以军旅作家群为例,说道:“50年代老一辈的军旅作家群,虽然说在他们成名于中国文坛的时候,昆明文联还没有成立,滇池文学杂志和昆明作家协会也还没有出现,但他们跟昆明市的文学队伍创立是有一种直接联系的。”紧接着他表达了对昆明作家队伍之未来的高度期待,他认为昆明汇集了全省的人才,它的文学力量肯定也是非常大的。昆明文学不是要做云南最好的,而是要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力量,“我相信今天在作协的接力棒交到陈鹏手上以后,他带着他的队伍会把昆明文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接着,主持人邀请四位作家对自己的创作进行分享交流。
陈鹏:为了昆明文学,为了写得更好,把自己撂在手术台上,又确乎是值得的
陈鹏表示,在他看来小说本是一己之私,大多写作者是写给自己的,跟外部世界并没有太多关系。但同时他又提到,“为了昆明文学,为了写得更好,把自己撂在手术台上,又确乎是值得的。”他感叹到,谈论自己的小说是极其困难的,“文本就在那里,任何一个人看到读到,都有论述的自由。要么喜欢,要么讨厌,要么认同,要么无感。说到底,作品发表、呈现之后,作家应该沉默,不必为它再说一句话,一个字。任何围绕自己写作的辩白、解释都可能是乏力和乏味的。”陈鹏也真诚地分享了自己小说写作的标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海明威、纪德、福克纳等一些伟大作家,“你可能永远无法企及,但试图和他们打上几个回合才是一个有抱负的作家该干的。”陈鹏还表示他在写作中会刻意回避宏大的主题,因为他更想呈现的是宏大之下的微渺个体。此外,陈鹏还提到了后现代时空里,中国作家所面对的写作困境,“我们面临着想象力枯竭的非难和考验,又必须小心规避某种简单的新闻式的肤浅,如何把握,如何深入,如何超越,用什么办法超越,是摆在每一个作家面前的难题”,但面对困境又如何呢,“只有写,尽量多的写,尽可能有难度地写”。
包倬:我就是一个凭感觉在写作的人
包倬在谈到自己的写作时表示自己就是一个凭感觉在写作的人,“在无数个夜晚写作那种感觉就像是暗夜行走,一个人在一个夜晚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走。有时候写作会把你带上那个沼泽泥潭,但是有时候它会将你带向水草丰茂的地方,带向春暖花开的地方,我特别迷恋这种写作的不确定性,我认为这可能是我写作最大的快乐。”他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写作心得可以分享,他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写,不断地建构一个个世界,随时迎接写作那种不确定性的快乐。
马可:所有写人的文学作品,都写的同一个男人和女人
谈到写作,马可认为写作首先是行动,所以必须将“写”付诸行动,并且是长期的行动。同时,她表示小说虽然是故事,但远不止于故事,而是以故事的形式呈现了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传达出了人所面对的具有普遍性的境遇,“好的小说是无用的艺术品,它不是工具,我甚至认为,凡是把之当成工具的作家,都没有济身于世界最伟大作家的行列”。马可认为,所有写人的文学作品,都写的同一个男人和女人,写的都是人在这世界的周而复始的流转。最终小说带出来的则是一些超出故事本身的东西。对于自己的写作,她表示很高兴自己可以书写和记录,“这种书写和记录,让人的生命不仅仅在滔滔河流里瞬间出现又瞬间熄灭,而是让它具有了一点痕迹,而这点痕迹也正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一点佐证”。
祝立根:我的诗歌具有着抒情的底色,也有着呐喊的动因
祝立根谈到当他放弃了坚持多年的绘画后,是诗歌给他救赎。他说,“我的诗歌具有着抒情的底色,也有着呐喊的动因。”他认为绘画给他带来了两个恩惠,一是审美的偏向,二是完成了早期的文学阅读,为他的诗歌创作打下基础。谈到他的诗歌创作,他觉得他的诗歌越来越贴近自身的现实生活,同时他也希望自己未来的诗歌语言能够像巫师喊魂那样,具有招魂和驱魅的能力。此外,参加《诗刊》的青春诗会得以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诗歌路径有些狭窄,他开始有意调整自己的创作,并坚定未来的创作方向:“故乡和他乡的边界正在慢慢消失。我应该书写故乡和自己熟悉的生活了。”最后他说道,“我知道诗歌这条道路艰难异常,但我也知道,这是我唯一的路途,我希望在那儿,能够遇见一个内心中的自己,和远处满城的灯火。”
随后便迎来了本次研讨会最精彩的环节——批评家对作家作品进行评论。
耿占春:“生为鲜花,死为蜜”说出的也许正是诗人的命运,也是作家的命运
耿占春先是提到丹增书记对云南写作的整体梳理,让他有了清晰的文学版图。谈到陈鹏的小说,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陈鹏非常崇拜马原,耿占春笑言他甚至觉得陈鹏的小说已经超过了马原,他认为陈鹏的写作已经掌握马原精髓,而且还融进了自己特殊的语言、故事和氛围。“阅读陈鹏的小说,让我感觉他的小说里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动机,有时候你可以把陈鹏的小说看做是元小说,比如《麋鹿》,还有《我和马原在洞庭湖底》,以及《天门的陆羽》,都是对如何写作以及作家对心中伟大作家的写作与生死之谜的探索。”而且陈鹏的小说还经常体现出写作与文字对人类的重要意义。“生活世界在陈鹏的笔下已经是一个破碎的世界,也许因为他踢足球,他的语言、叙事节奏和情节的整个进展都很给力,都很快速,不等你对一个小说的阅读产生疲倦,他就迅速的转向了另一个情节,他也不会沿着一个线索一直讲述,而是不断变化,我想可能足球的技法也融进了小说的这个领域。”陈鹏总是拒绝自己的小说走向通俗,他的小说所探讨的,是什么力量让生活变得破碎,而他为这个破碎的生活赋予了意义。
这种生活的破碎感也体现在祝立根的诗歌中,祝立根的诗有小说式表达和随笔式的表达;陈鹏的小说还具有某种诗性,某种层面上,他们的作品有很多共鸣的地方,只是文体不同。不同于小说,“诗歌是把无意识经验包含进来的话语结构,所以它是非线性的,是一个体验的连续体。诗歌表达一种经验的时候,不仅是在意识层面,还要深入无意识层面,变成一个经验和体验的连续体表达,而不是仅仅把体验限制在意识层面的表达。”最后他引用祝立根的一句诗,“生为鲜花,死为蜜”说出的也许正是诗人的命运,也是作家的命运。
张定浩:从悬崖的边缘再往前走一步,那一步才是我们自己
张定浩首先对祝立根的诗歌进行了评论。他认为祝立根的作品其实是很典型抒情诗风格,并且他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个人特征。他特别指出祝立根诗歌中的“身体式隐喻”:“他的诗歌会出现骨头,出现各种各样的感官,包括泪水,这样以一个人的身体去面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对冲。他的节奏也是非常激烈和快速的,可以把你迅速裹挟进去,所以读他的诗歌还是非常有快感的。”同时,张定浩也非常真诚地分享了自己对祝立根诗歌的另一些看法,他认为当一个诗人一直依赖于某一种模式或结构往前推进的话,会有一种重复感。他表示祝立根推动诗歌前进的始终是一样的东西,始终是一个自我的东西在推动。“他虽然是在写万物,但他很多时候呈现出来的,让我们看到的还是诗人自己,而不是说真正的万物世界。”不过他也表示在祝立根近期的诗歌里也可以看出他在寻求某种突破,“在某一刻意识到这种风格的局限性,他就会期待自己成为另外一个人,他永远不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人,但他期待另外一个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方向的一种张力会促使他的东西有所变化,会让他东西变得更加强大。”
对于马可的小说,张定浩首先表示他很喜欢马可写小说的那种从容和耐心,尤其《翻越阿尔金山》这篇,他很喜欢马可对对话的经营,“她可以很耐心地展开一个对话,这个对话不一定是为了推动一个情节,她就是为了呈现生活本来的面目,就是那种毛茸茸的细节”,同时他认为马可对于男女之间情感微妙的变化把握得特别好。但同样的,张定浩也指出了他阅读马可小说时的一些遗憾,“如果说立根兄一开始的诗有某种模式感和重复感,我觉得马可的小说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他表示他很喜欢《看护》,写了一个七十多岁女性的性意识,但是当写到这个女性和她的看护之间的微妙关系时马可却停在了某个地方转而写其他生活琐事,他更希望自己能看到马可在写到自己想要抵达的那个点之后再向前走一步,“短篇小说有时候要避免自己陷入一种抵达高潮之前的那种快感里面。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要写什么,我们再往前走一步,从悬崖的边缘再往前走一步,那一步才是我们自己。”
马兵:对于人生的本质性关系的发掘和呈现,包倬和陈鹏的小说是有汇通之处的、
马兵主要是对陈鹏和包倬作品的研讨,谈到陈鹏的小说特质,他认为,陈鹏虽避免了宏大的主题,但其实提供了某种更本质化的,对于人性或者说存在境遇的一些观察。而且陈鹏很在意故事和叙事均衡,体现了叙事智慧。此外,陈鹏还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建立起一种均衡的关系,这体现了陈鹏作品的深刻性。
谈到包倬的作品,他认为包倬懂得小说隐与显的辩证法,非常擅长在一个小情境里把大的波澜做出折射来;此外,包倬非常擅长写两人的关系,两人关系其实代表着人类最本质化的关系,所有的关系都可以从两人关系里面衍生出来,也就是说包倬的小说也是有对于人生的本质性关系的发掘和呈现的,在这一点上,马兵认为包倬和陈鹏的小说是有汇通之处的。
王朝军:我总想让小说有一种溢出或者一种越轨
对于包倬的小说,王朝军承接了马兵“两人关系”的论述,表示在小说的两人关系中其实还有第三者,也就是叙述者这个主体。由此他谈到拉康的镜像理论以及人的自恋性。他重点谈到了《红妆》这篇小说中女主人公被假想出来的主体位置,“她的这个祖母、奶奶和她自己其实是处于一种被看的位置,一个客体的位置,但是她们依然想要形成一个主体的表达。但是我们最终会发现这种主体的表达会陷入了沉默,也就是说当发现这种表达不可能,这种表达其实是一种虚妄的时候,这个时候作品的意义才出现。我们往往是在那种发现拯救的不可能的时候,可能性才会更多一些。”同时他还表示自己很喜欢包倬小说中的那些比喻,这些比喻呈现出一种强大的力量感,让他震惊。
谈到马可的小说时,王朝军表示马可的写作显得特别游刃有余,特别自如,无论选取任何一种生活的截面或者片段,她都可以通过这种自然的日常叙述中去窥探,或者说去表达女性本身的一种困境。但同时他又指出他总想让小说有一种溢出或者一种越轨,或者说要在既有的轨道之上我们要火车不仅仅到站而已,希望通过那个站头去寻求更多的可能性,或者说寻求更真实的一面。
不知不觉时间已超过原定结束时间,即使到了午餐时间,大家仍对这场文学盛宴恋恋不舍,似乎文学已足够饱腹。好在,下午还有一场文学大讲堂,可继续滋养和充实大家的文学精神,欢迎跳转二题查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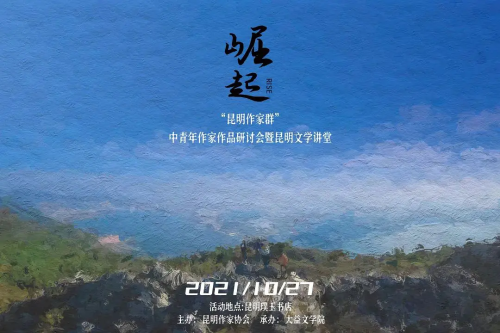

![}0JXOV%DJ%QS@WXTA$]YE2B }0JXOV%DJ%QS@WXTA$]YE2B](/upload/resources/image/2021/11/17/3567239_500x500.png)
![D}]U_G}LSS`}}39$OKI(}EE D}]U_G}LSS`}}39$OKI(}EE](/upload/resources/image/2021/11/17/3567242_500x500.png)



![[S(`W]BGVTG$W9E3$Y%_[P1 [S(`W]BGVTG$W9E3$Y%_[P1](/upload/resources/image/2021/11/17/3567246_500x500.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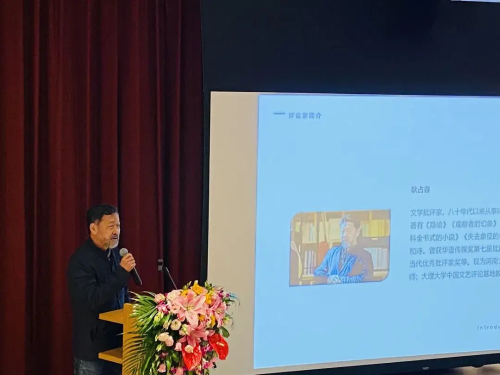

![Q})3T5CL_T9S~)]K3BYO@5J Q})3T5CL_T9S~)]K3BYO@5J](/upload/resources/image/2021/11/17/3567252_500x500.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