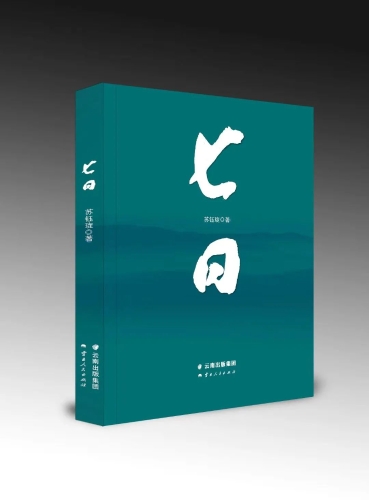彝族青年作家苏钰琁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七日》(2022年6月云南人民出版社)运用巧妙的叙述技巧,讲述了一个完整、意蕴丰富的故事。小说以普洱“民族团结碑”为背景,歌颂了这一段血祭南疆、可歌可泣的英雄历史。其叙事结构、叙述视角以及反复出现的意象,具有宽阔的文本阐释空间,尤其是“太阳”的出现,具有多重隐喻。
一、 隐喻中的“太阳”
小说中的太阳穿插在李保的现实和回忆两个世界之中,同时李保也在两个不同时空中遇见太阳。当李保思绪从回忆或梦境回到现实时,发现太阳没变,变的是自己,便颇有“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的岁月感、沧桑感。回忆中的太阳简单明快,现实中的太阳蕴藉丰富,由此构成了诗性的太阳。
首先,回忆中的太阳常用于环境描写,暗示危险来临、亦或烘托紧张、宁静等氛围,这是诗性的表现之一。如:“山梁的一横绿色,让毒辣的日光照得煊赫,此时绿横上冒出一穗子橙红,正一颤一颤地往上升。” “全部人都张望着缅甸方向的那抹橙红,屏息凝气。”盛夏的正午理应是休憩的好时光,但众人却在勐冒山上张望着同一方向。这体现了紧张的氛围,也预示着史大人会给西盟带来危险。又如:“黎明的空气总是泛着微微的蓝色,使得那初初降临的日光,仍带着一丝清冷。”梦魇后的混沌中(鉴于李保虽梦醒,但思绪仍停留于梦中,因而将此处的太阳归为回忆一类),李保便“已我观物”,即便是那破晓的第一缕阳光也夹杂着凄凉。虽此处未对环境进行客观描绘,但作者从感官入手,引领读者自由建构其凄清寒冷的画面。再如:“落日残留的长影,染得天际一片血红……给绿莽莽的山林披上淡淡磷光。……暮色便暗淡了。” “天上月面朝东,凸月刚显……薄薄的金光铺满山岗的时候……”前者在严春帮村民渡危险,取得李保信任后,用落日残影写出了夜晚的宁静和谐;后表现了严春说服李保等人参加国庆典礼的后的欣喜。
其次,现实世界中的太阳常与其他形象联系,构成隐喻,从而拥有多重阐释空间,这也是诗性的表现。第一,太阳(光明)与黑夜(黑暗)二项对立的出现,增加了太阳的表达张力。在阴阳之间,太阳抽象出希望之意,不仅仅指称具体事物了。如:“荒郊野外的光明,全部都要仰仗太阳。当最后一丝天光散尽,黑夜便像浓雾一样将人包裹起来,从身到心,统统纳入暗世界的管辖。”此处意指李保希望逃离鑫副官的魔爪。再如:“热辣辣的太阳一照,丝毫见不到黑夜的痕迹,但是黑夜真的没有降临过吗?……李保没能和太阳一同醒来。”此处太阳意味着生命。第二,太阳与树木一同出现。《茶诱》篇作者将李保比喻成西盟大地上的树木,世世代代在阳光的照耀下伸展根系。在汲取养分之时,太阳已成为树木身体的一部分。犹如李保的先祖世代在这土地上日出而落,日落而息,太阳俨然已成为指示物而存在,同时也会在祖先的身体上烙上印记,即干燥粗糙、黝黑的皮肤。因而李保认为自己是生活在阳光下的树。再结合“太阳升起的那一刻,终于看清了共产党的真心,认清了前路的方向。”太阳的隐喻不言而喻。这棵树不忘其本,保持初心,始终在阳光的滋养下成长。
第三,太阳与月亮成对出现。太阳和月亮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中都有特殊的象征义。这主要出现在《曰归》的民歌歌词中“只见太阳呵,出了又落,落了又出。只见月亮呵,胖了又瘦,瘦了又胖……”以及“他仿佛看到了云层后的月亮,甚至看到了月落之后升起的太阳。想到月亮冷冷的清辉……再想到太阳,那光芒万丈的太阳,他却觉得悲凉。是呵,他还能再见到太阳吗……”前者出现在《曰归》章的开头,以拉祜女人幽婉的歌声为此章定下命运悲凉的情调,同时也与题目“曰归”有异曲同工之处。太阳与月亮不断经历轮回,每日太阳带来第一缕阳光即意味着万象更新。新的一天,新的生活,此时人们暂时忘记了黑夜。但若某天黑夜里,你不知能否见到第二天早晨的太阳,心情或许凄凉、伤感,或许会突然感叹这就是命运吧,生于黑暗,沉于黑暗。此处太阳与月亮的结合多少携带着命运的悲凉感。结合“不论世间人心变换几多,到了既定的时间,太阳依旧照常升起。”更能体会其中的宿命感。
由此可知,作者并不是随意选择第三人全知视角进行叙述,而是为了能重新结构李保在线性时间上发生的故事,从而将作者思想蕴藏在其中,呈现出复杂的韵味。
二、 寻找光明的眼
基于在文化的积淀中,太阳最明显的隐喻之一是光明;在《迢途》一章出现的“咽下最后一口离别的酒,受洗的灵魂睁开了眼睛,新的太阳升起来了”;以及在读者的阅读和生活经验中,眼睛常与追寻光明有关,如诗歌“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因而引出本文的第二部分聚焦于“眼”的阐述。文中的“眼”是具有诗性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者在小说中赋予“眼睛”特殊的任务,即体现西盟地区的自然地理风貌以及村民的辛劳淳朴。其实现途径是通过将眼睛比喻成切实可观可感的形象,从而引领读者自由建构对西盟地理环境、生活方式的认知。如“普似夺眨巴眨巴一双小豆眼”“裴阿欠眼袋乌青发肿,像是挂了一对小核桃”“黄澄澄的大眼睛陡然凑近,一颗黑豆似的瞳仁如同子弹一样向李保射来”,另外作者还将其喻成乌梅、黑葡萄。可见西盟地理环境复杂、温度适宜、日照雨水充足,才足以同时养育这些植物。另外文中还将“眼”做了如下的比喻:“拉勐两条泥鳅似的浓眉毛,弯曲蜷缩着”“睁大他宛若鹰隼的双眼”“拉勐双眼布满了蛛网似的红血丝,眼皮也肿得像两条蚕蛹”“头天人们都没睡觉,个个像猫头鹰一样盯着他,眼睛泛着瘆人的绿光。”“舒云聪盯着一对兔子眼睛”。此处将眼睛比喻成动物,便于更进一步融入西盟的环境。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者生于西盟,成于西盟,因而将熟悉的事物内化于作品也是不足为奇的。这些形象的出现便在读者脑海中不自觉呈现出西盟人民养蚕耕地、割草喂兔等画面,从而得出村民辛劳淳朴的品质。
其次,眼睛在小说中还承担着另一功能,即为厚重严肃的叙述灌注一丝清凉。文中对于眼睛的描绘不仅仅体现在静态的比喻,作者还善于运用大量的动词进行呈现。使整个故事在一张一弛中有序进行,严肃不失温馨。如第一章写孩子们在饥饿中等待父亲时,母亲娜葐“用一双乌梅似的大眼睛巡逻着”防止调皮的孩子偷吃,作者用“巡逻”一词将母亲的认真与警惕呈现了出来。而后,妮轰用自己惯用的战术获得一大勺酸笋烂饭,妮轰的眼睛“唰地亮了”。小女孩的易于满足与母亲的疼爱在这样的场景下便不言而喻。不管是娜葐和妮轰、木香和阿明还是拉勐和妮轰之间,都是通过双方的眼神交流达成温馨氛围。亲情为紧张的叙述增添了一丝温情。不仅是亲情,文中的友情、爱情、民族情等都值得读者深入挖掘。
再次,小说眼睛的诗性还体现在“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睛能直击要处,呈现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以及思想境界。李保从最初的眼神炯炯,面对危难神态自若、目不斜视,到“眼睛干涸枯朽,像离岸太久的死鱼,没有一丝活气”再到“最后一滴眼泪被埋进泥土时,眼睛看得更亮更清。”正是作者擅长这种功夫的体现。从局部来看,文中有几处眼的描写不容忽视。《罗网》中“李保面色黝黑,高颧骨,大鼻头,眼下一对深深的眼袋……唯有那双眼睛,平静看人时,茶色的瞳仁映出火光,跟眼窝一起深陷进去,黑暗中只漏出海上的一点孤灯,叫人辨不清方向。可当他笑起来,鱼尾纹将外眼角划开,一双眼睛便十分锐利……李保此刻的笑又有些许不同,他眼中不起波澜”此处作者转换了叙述视点,以屈洪斋之眼为取景框,为读者呈现李保的模样,便于读者更好触摸到独立世界中的人物。在蒋匪屈洪斋眼中,李保虽是个皮肤黝黑的老头,但其眼睛给人带来的震慑直击心底,崇敬之情便油然而生。更何况作为读者呢?《犬杀》中详细写了在李保眼中严春的眼睛“如寒星,如秋水,如两条黑鱼游进了两潭白水银”,随后继续写道“严春眼睛清澈,目光像一泓清泉,似乎能够照透人心”。人的善恶能够从眼神里分辨出来,严春因为心灵的纯净让其眼睛清澈得像一泓清泉,不似恶人的眼睛,所以李保便对他放下戒备之心,进而严春获得了李保的信任。文中的眼睛如太阳意象一样贯穿于全文,除了刻画人物外貌,还有许多丰富意涵等待解读。
诸如以上种种,太阳的隐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寻找光明的眼,体现了小说的诗性意蕴,同时也是小说艺术价值的体现。(《昆明文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