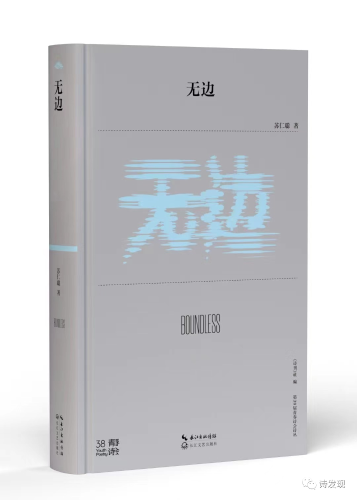作者简介
苏仁聪,1993年生于云南镇雄,青年诗人、青年作家、大学教师。作品见《诗刊》《中国作家》《北京文学》《诗收获》《星星》《草堂》《扬子江》《边疆文学》《西部》《飞天》《百年中国工人诗选》《2019中国诗歌精选》等。参加第十一届星星夏令营,第38届青春诗会。出版诗集《无边》。现居山东。
苏仁聪首部诗集《无边》于2023年1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阅读推荐
苏仁聪是一个诚恳的在场的记录者,亦是一个努力呈现真实的思想者。他和他的文字始终处在挺进、停顿、送抵的循环与反对的道途中。无中生有和别开生面的灵性写作,使其诗歌具有了多向度的亦真亦幻的美学品质。
——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书法家雷平阳
带着青春远游的时光,呈现出一个青年人来自诗歌的忧郁和光芒的情怀。苏仁聪的诗歌,每一首都是油画、时光,原乡,他的情绪变幻出地貌,波涛和蓝天白云,这是一组丰厚而年轻的诗歌,语境幽转,正带着心灵幻想的力量,抵达远方。
——著名诗人、作家海男
苏仁聪的写作似乎一步跨越青春期抵达平静、沉稳的中年,在他的身上,活着一个从古典中国轮回过来的人,那个人曾经行步于中国西部并与那片土地有过深情的交流。他的写作,舒缓而迷人,久远年代的记忆在他笔下一一醒来。
——著名诗人、画家安琪
新世纪涌现出来了众多优秀青年诗人,苏仁聪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整体来说,其诗歌写作呈现出清朗、明晰、稳健的风貌,其专业性与纯粹性也证实了逐步的成熟。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正是这样,苏仁聪诚实地践行着这条朴素的真理。
——著名翻译家、诗人李以亮
形散而神聚是苏仁聪诗歌比较显著的特点。他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中,乐此不疲地将自己松绑,打散,其目的是为了寻找并确认出一种新的心灵姿势,以便更好地接纳诗人独有的生命体验与表情方式。当然,他找到了,从汉语中走出来,戴着荆棘编织的王冠。
——著名诗人王单单
读苏仁聪,感到他是一个有故乡的人,在他的诗中,同中国许多在乡下的人去了城里一样,四处奔波,无处落脚,但他的故乡在他心中的美丽烙印他无法忘记,纵使他在一遍遍地写着他乡也是在写着故乡。苏仁聪很年轻,如此年轻而又如此热爱自己故乡的诗人并不多见。他的诗大都写那些有温度的老事物,他爱它们,它们就是他的诗。
——著名诗人杨键
对生活细节的敏感,使作者可以迅速地捕捉到那些看似无关紧要,实则有丰富蕴藉的事物与情境,以特有的视角、精准的语言去完成表达。苏仁聪的诗围绕对各式苦难的体验,展现了他的灵悟与慧心,饶可回味而富于表现力的句子,也给人深刻印象。(包商银行诗歌奖授奖词)
—— 著名评论家、诗人张清华
“一首诗里应该装有一群人的命运”,苏仁聪的确在他的诗里做到这一点。诗的语言往往被认为应该是优美的,然而一旦和严酷的命运发生亲密的接触时,诗人们往往会陷入两难的境地。面对命运,诗的语言是否仍要一味优美呢?苏仁聪的诗看着不一定那么优美,但的确做到了一个诗人在面对人的命运时应有的诚实。他的诗直面现实的艰辛,有悲叹,有哀伤,但更有直面人生痛楚的勇气。(包商银行诗歌奖授奖词)
—— 著名诗人、北京大学教授臧 棣
在诗的叙事方面,西南诗人与西北诗人截然不同。都是灵魂的“边疆书写”,西北诗人高亢悲壮、挺拔突兀,西南诗人的叙事则像热带雨林一样潮湿茂密。即便他们要叙说的“灵魂”高如大象,体现在语言层面的“行动”也迟缓一些,诗的“脾气”也较为温顺。苏仁聪就是如此的安静叙说者,词语和节奏的搭配,意象和物象的寻常,风格和思想的散淡,都带有明显的诗的“亚热带”的特征。这让我无端地想起艾芜和《南行记》。曾漂泊于滇缅边境的艾芜,为中国文学的西南叙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样本。这种“西南叙事”,不仅体现在迥异的生活哲学,或者较为天然的生命形态,更是体现在这个文学溢恶的时代里,一个写作者对孤独的人性美的关照,从而为大西南建构了一个救赎与批判同在的文化空间。苏仁聪的诗,正是对西南文化空间的自觉的延续和完善。
——诗人、评论家原散羊
《无边》后记
这本诗集收录了我从2018年到2022年上半年所写的部分诗歌,它描绘出了我这四年的写作变化轨迹和心灵以及身体运动轨迹。2016年刚开始写作时,我没想过有一天能出版一本属于自己的诗集,那时我还是一名化工专业的本科生,只是把写诗当作缓解学习压力的一种方式。因此这本诗集的出版,对我来说,像是一个悠远的梦。考上石河子大学研究生之后,面对从未见过的风景,面对森林、草原、沙漠和一望无际的戈壁在同一片大地上出现,从童年时就栖居在内心的诗神便开始左右我的心灵,使我真正爱上诗歌。从此,我走上了诗歌狂热的写作道路,直到如今,直到将来......
我出生在云南省镇雄县西北部群山中的一个微型村庄,全村只有六七户人家,现在均已搬到集镇上。那个村庄被群山环绕,无边无际的森林给了我最早的诗歌体验,我和我的童年玩伴们每天游走在森林中,割草喂马。我最初认识世界时,只看到了世界上的森林和森林之上的天空,所以,那时我认为,世界单纯由森林构成。后来我到了外地上学,见到了城市中的高楼,车水马龙的街道,见到了戈壁和荒漠,雪山和大海,我对世界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但这种改变依然带着浓厚的森林影子。我们那里的森林中有很多杉树,在我们当地,杉树主要用途为打造棺材,每个人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去到一棵杉树中,这是我们当地人的归宿,无边的杉树森林里有一座座“空坟”,每次去到森林中,那种旷古的虚无和实在交织的感觉便会自内心升起。
所以一开始,我打算将这本诗集命名为《无边森林》,我希望故乡无边无际的森林能给每一个在人生迷途中和走向死亡过程中的乡亲以安慰。今年7月,在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的一个茶馆内和朋友们谈起这本诗集的名字时,一个朋友建议我将诗集名称中的“森林”一词去掉,留下“无边”二字,这样“无边”就会显得更“无边”。我觉得这个建议极好,在我的故乡,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无边的东西何止是森林,任何东西都是无边的,我们在始终在无边的世界里漂流。因此,这本诗集的名字最终定为《无边》。
这本诗集由四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总标题为“去边界”,这部分主要收录我在新疆求学时写的诗歌,这些诗歌大多都有浓郁的边疆风情,大量写我在新疆见到的风景和感受到的人文,以及沉浸在这种风景和人文之中的内心体验与生存体验,部分写我在新疆见到的那些普通的异乡人,他们和我一样,都漂泊异地。当然也有部分诗歌写的是我在其它省份的生命和情感体验,但这些体验和在新疆的体验有相似性,所以把它们放在一起。
第二部分总标题为“月光高速”。毕业后我回到家乡,又受疫情影响闲置在家半年后,第一次觉感受到了生存的压力。于是我和堂弟苏迪决定去省城昆明找工作,那晚我们开着车路过大关县和盐津县交界的大峡谷,高速公路被月光照得明晃晃的,我想起之前在求学时,每每经过这里回家,而现在,我走在和当年回家时相反的路上,感到前途渺茫,工作无定,于是有了《月光高速》一诗。这一辑很多诗歌都是在外省或漂泊途中写的,它们记录了我在不同省份漂泊时内心的深度体验,它们也记录了我遇到的很多陌生人,多年以后,我相信当我再读到这些作品,那些漂泊的日子,那些陌生的人都会重新浮现出来,让我的过去在时间的摧毁中保持坚固。
第三部分总标题为“我的小镇”。无疑这部分诗歌多数是在碗厂镇完成的,它们记录了故乡的风物,乡亲们的生存方式与存在方式,还有相当部分诗歌在追忆过去,我的小镇近些年变化极大,传统的生活方式,传统的住宅,传统的文化等逐渐被摧毁,大家都走向一种同质化的生活中,变得和北京上海昆明没有多大区别,我想通过诗歌细节的呈现,留住小镇上的过去。当然我还写到小镇上的一些典型人物,我认为,他们也是值得关注的。
第四部分是几首长诗,包括我在疫情期间写的《防疫日记》三首长诗,我力求准确地描绘出疫情初来时,百姓内心的恐惧,以及在封闭期间大家的焦虑与对抗疫情的一些行动,也间接透露出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对生死的看法。《山中笔记》也是在这一期间写的,但《山中笔记》主要想唤醒我对森林的悠远记忆。这些长诗试图处理短诗无法完成的一些主题,它们更能代表我在不同场景下的生命体验。
我不想在诗歌中表达观点,所以我的大部分诗歌都只是一种讲述,缓慢的讲述,我力求写出我们这个时代多数人的精神焦虑和精神狂欢(当然现在还远远没有做到)。我认为,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巨变的时代,世界逐渐一体化,那些地域特征逐渐消失,传统的乡村也逐渐消失,我们活在一个深度异化的大时代中,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孤独。
诗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诗歌在帮助我们重新建设那正在坍塌的精神世界,语言是我们思考的核心,是我们思考的形式,通过语言,诗人能重新发现深存于基因中的古老记忆,从而更好洞察当今的社会,诗歌让我们得到真的感情,真的生命体验。
一个诗人最伟大的使命是真实记录他所生活的时代,那么,我们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中呢?首先,正如我之前所说,这个时代正在朝着一种模式发展,多元性正在丧失,传统的乡村正在解散,山乡正在发生巨变。现代信息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使我们再难关照自己的灵魂。我的祖母在乡村生活了七十多年,最近几年,我发现她也变成了一个“时髦”的人,以前她总是在田间地头散步,现在,一有空,她就坐在沙发上刷抖音。有一次,她居然问我,美国因为疫情死了这么多人,为什么美国人没有造反?我说奶奶,在美国,造反叫下台,她说,对哦,特朗普下台了。我非常惊讶,一个寓居乡村的老太太,不再去侍奉她的神灵和她的乡村,反而关注起世界来。她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那个乡村的一个典型老人,正是高度发达的信息和交通使得她的旧世界崩塌,使得她的新世界重新建筑。
那么要如何去书写这个时代呢?在我的观点中,我们应该关注生存在这个时代上到士大夫下到拾荒者的每一种人,我们真实地去记录他们的生活,真诚地去关照他们的生存。另外,我们还应该关注这个时代的每一种新的意象,诗歌是发展的,不是一尘不变的,在唐宋,有月亮、有花草、有落日有晚霞,在今天,有AI、有高铁、有飞机、有工厂、有社交软件有歌舞厅,这就是构成我们时代的元素,我们不应该回避,应该直面。
人类的贪婪造就了我们现代生活的一切,人类的贪欲还在膨胀,沿着一个个台阶上升,这不能怪每个具体的人,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造成的。也并不是坏事,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在这里丢失了我们的灵魂。
诗歌恰好是一种伟大的指引,它给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我们在纷繁的世界中看见我们的灵魂,知道我们的孤单,知道我们内心深处最本质的“还乡”欲望。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前女友范贤顺,她是我写作开始道路上的重要支持者,我们好了很多年,因为各种原因最终分开了,她见证了我诗歌写作的“从0到1”,我们在一起的那些年,她读过我写的每一首诗。很多时候,我们两地分居,我就在电话里给她读诗,她常常以一个非诗人的身份给我的诗歌提出修改意见,许多意见都使我受益。因此,这本诗集,我愿意献给她,并真诚地祝她幸福。
还有很多良师益友,他们时常鼓励着我继续写下去,感谢遇见他们。
最后,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故乡,镇雄县碗厂镇,它用它灵秀的风景和粗野的文化教育着我。作为一个诗人,我们必须不知疲倦地去认识这个世界,在接下来的生命历程中,我必定要不断出走,但也必须不断返乡。就像大海里的水,当它们蒸发之后就以雨水的形式降临到世界各地,但它们还会通过河流回到它们的故乡大海。
人也一样,我们需要出走,也不得不返乡。
也许有一天我会不朽,但我首先会在我的故乡不朽;也许有一天我会被人们遗忘,但我最后才会被故乡的人遗忘。
我将继续带着极大的热情去读书和写作,去关心人类,关心草木与天空,去完成一个诗人的伟大使命。
苏仁聪
2022. 7.14于香格里拉
2022. 8.28改于驻马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