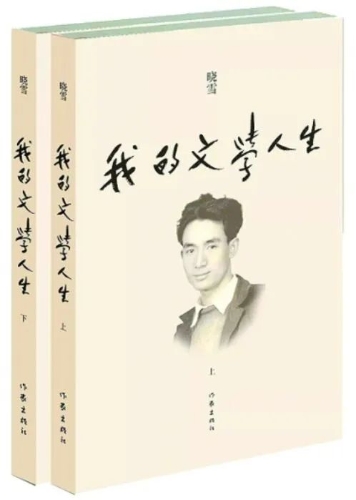说什么和怎么说(之二)
——以我在晓雪研讨会上的发言为例
冉隆中(文学批评家 现居昆明)
我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我对面、近在咫尺的晓雪。我看见晓雪前倾的身子更靠前了,他眼里也有了诧异的神色。
他惊诧的神色点燃了更多人的惊诧,这让我想起了一段谚语:一个人敢当众说假话,是因为他知道周围没有人会证实他;而一个人不敢当众说真话,是因为他知道周围没有人会支持他。一个社会可怕的不是假话的甚嚣尘上,而是真话的普遍沉默。但我还是忍不住继续说了下去:
我知道,这样来评价晓雪的诗歌成就,多少有点刺耳,有点不礼貌。但这确实是一代诗人共同的宿命和悲哀。很多诗人作家的才华,被浪费在了一些不值得的地方。究其原因,可能与他们的精力过多地用在了歌唱所谓的“运动”(比如“反右”、“四清”以及特殊十年等等)有关。这里的“运动”不是体育,而是关乎观念的一种社会进行时态。在过往经历中,每一个时间段,都人为设置了的无数“运动”,用以安置或调遣人们的思想观念。置身其中的作家诗人,其实经常处于被裹挟的被动状态,既不能很好把控自己的写作姿态,也很难正确辨别“运动”的真伪善恶。如果对这样的东西一味歌唱,就很易丧失创作的主体,很难在创作上留下经得起时间淘洗、历史检验的特别好的作品。这个经验教训绝不能重演。虽然这个话题不适宜在今天这个场合展开总结,但值得文学创作道路上所有后来者充分警惕,认真记取。
说到这里,我稍微停顿了一下。尽管我声音依然洪亮,但内心却没来由地感到空虚。我已经没有勇气将目光与面前的晓雪对视。就像为了自圆其说,我做了如下解释:
套用前述那个关于郭沫若诗歌评价的说法,其实不是我的本意,而是典出于晓雪的自我评价。记得,若干年前,有一位文学老人为自己祝寿,遍发英雄帖,请帖上写着非常醒目的一句话,说他“创作发表了一千多万字的文学精品”。对此,晓雪跟我说:一千多万字,有没有,不知道。但一千多万字的文学精品,肯定没有,不可能有。古今中外,作家诗人,有一两首诗,一两篇代表作,能够传世,青史留名,就不错了。我的作品,如果有几句话能被读者喜爱,有一两篇作品能被你们批评家记住,我就很开心知足了。晓雪这段话,我写在当日的日记里,我认为,这既是晓雪严于律己的一种态度,也是寄望于文坛,对任何人的文学成就,应当力求客观公允的作出评价。这段话对我影响很大,我愿意在此分享给大家。
后面我还滔滔汩汩说了很多,关于晓雪的散文和评论,关于晓雪这个人,他的勤奋,才华以及诚实的人品……说到晓雪写人记事的散文,那种冲淡平和,不事雕琢,素朴优美的文风,我说,它影响了我和我的朋友,也影响了很多读者。举个例吧,很多年前,广西地界,有一个当过警察、公务员、小老板的文青,有一天他从《人民文学》读到写大理鸡足山的一组散文,这些散文醍醐灌顶般让这个文青得到了觉悟,也如一棵树撼动了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了另一朵云,居然影响到这个文青千里迢迢直奔鸡足山而去。从此,江湖上少了一个文青,鸡足山多了一个沙弥。这个小沙弥经过苦苦修炼,居然成了鸡足山如今的住持大方丈。有一天,一群文人上山采风,正巧碰到大方丈亲自接待,交谈中,方丈突然问起,你们有谁认识一个叫晓雪的作家吗?然后说起自己这段与鸡足山结缘的往事。坐中恰好就有认识晓雪的,掏出手机就连线了晓雪,于是,方丈和晓雪——两个素未谋面的人,从此开启了一段非常特殊的善缘。
这其实也是微叙事。巧的是,我说到的那位在鸡足山顶掏出手机让方丈与晓雪连线的作家,此刻也正置身会场,他从侧面后排站起来,纠正了我叙事中一个小小的口误。他是纳张元,现任大理大学文学院院长,也是云南作协现任副主席。
会场发言的微叙事是一种讨巧的技巧,它总是优于那些夸夸其谈让人不着边际的宏大叙事,但它依然低于哪怕粗糙不中听的真话。如果开会发言或说话艺术也自成一个美学体系,那么它的头部或顶端,肯定是由真话系统构成的,微叙事最多居中,不着边际的宏大叙事则应该垫底。但现实中关于“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通行规则和评价体系,刚好颠倒过来。
但当时我无心于会场里所有人对我发言做出的任何评价和反应——我只在乎坐在对面的晓雪,在乎晓雪听到由我嘴里说出“雪老确已老,诗多好的少”之后,他的心里,会不会留下阴影?如果会,这个阴影面积会有多大?我最耽心的,是他在大病未愈的高龄,对批评之声的接受程度。虽然我在后面发言中准备了足够的也是诚意的表扬,但在这样一个与其说是对某部作品的座谈研讨,不如说是对老作家一生文学功绩加以总结定论的庄重场合,像我这样哪怕只说了少量的诚实的批评的话,是否恰当,是否应该,是否必须——我并不清楚。
所以,至今,我的内心,依然十分忐忑。
2023年3月31日 昆明初稿
2023年5月18日 改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