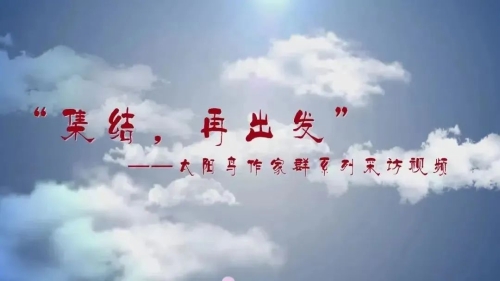简介
辛勤,云南省少先队队报《蜜蜂报》创办人,原主编。2000年任云南省家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2005年获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等十部委颁发的中国青少年社会教育银杏奖突出贡献奖。现任《昆明日报·家庭教育文摘》主编。创作的童话作品《一块奶酪》被教育部选入统编教材小学三年级语文上册。
Q:辛勤老师,您在童话《一块奶酪》中塑造了蚂蚁队长这个深受小朋友喜爱的形象,请简要谈谈创作这个形象的初衷。
辛勤:《一块奶酪》是一篇童话。1994年在《北京日报》小苗副刊发表。人物非常简单,蚂蚁队长,一只小蚂蚁以及众多的小蚂蚁。蚂蚁队长这个形象最大的优点就是说到做到。他不是没有私心。不是没有欲望。不是不想占有,而是受到诱惑的时候,他会自我教育,自己战胜自己。孩子们喜欢他,就是因为他真实。我到山西、湖南、四川、云南的很多地方,听小朋友反映,他们都喜欢蚂蚁队长。在这篇小童话中,蚂蚁队长一共发布了六个指令,第一个指令:今天只许干活,不许偷嘴,谁偷嘴就要受罚。这个命令发出之后,所有的小蚂蚁都听话。只有一只小蚂蚁嘀咕:“要是偷嘴的是您呢?”蚂蚁队长毫不含糊地说:“一样要受处罚。”这就把这道指令下死了。有趣的是,蚂蚁队长在搬运奶酪的时候,特别卖劲,用力过猛。把一小块奶酪渣子弄掉了。这一来,诱惑产生了,蚂蚁队长的心思动起来了。这点奶酪渣,扔了可惜,想吃而又不可以吃。这个时候,蚂蚁队长下了第二个指令:大家原地休息。他趁机动起了脑子。结果发现大家休息的时候,都不愿走开,心思都在掉了的那块奶酪渣子上。蚂蚁队长一生气,下了第三个指令:哪里凉快到哪里去。他想把大家支开,可是一看大家都惦记着那点奶酪渣子,就发出了第四个指令:稍息立正,命令大家向后转,离开现场。当蚂蚁一个也看不见的时候,他的心思七上八下,这个时候贪嘴,谁也看不见。这对蚂蚁队长来说就是最大的考验,身边没有监控,他还能不能说话算数?嗅嗅那点奶酪渣子,真香,不要说吃,闻闻都舒服。终于他想起自己说的话,想起了那只小蚂蚁的嘀咕,一跺脚,毅然站在石头上面,下了第五道指令,把大家召集回来。大家走拢来了,所有小蚂蚁的目光都是第一时间盯着那个奶酪渣子还在吗?结果发现还在,大家就松了一口气。这时候,蚂蚁队长的第六道指令下了:这点奶酪渣子,丢了可惜,让那最小的那只蚂蚁把它吃了。
这么一篇童话,我想告诉孩子们,诱惑随时会产生,生活没有诱惑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人,没有欲望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有欲望而碰到诱惑产生的时候,要守住自己的良知、良心、良能。
我认为这个品质一旦在童年深深地扎根在孩子心里,人格形成就有了底气,做人的良知、良心、良能就有了根。他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就会真正地增强。这等于为他终身的成长塑了一个保护神,这样的孩子将来长大了,不管面对什么样的诱惑,他内心都会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形成屏障。
人没有欲望是不行的,不要否定欲望的力量,有欲望才有积极性,有欲望才有生命力,有欲望才能够有青春。只是有欲望而又产生诱惑的时候,要经得起考验。
我配套写了一篇小文章叫《心灵的刹车》,每个人心上都有一个刹车,这个刹车就是良知,良知是人与生俱来的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你是人,你有人性,你就应该有良知。良知不行了,人们才强调良心,良心不行了才强调良能,良知、良心、良能都不行了才强调道德。道德是什么东西?道德只起一个作用,调节欲望,抑制破坏性情感。所以当人不能调节欲望。不能抑制破坏性情感的时候,就需要道德来约束人,调整自己的欲望。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首先要培植的是良知,还不是道德,道德是第二位的,有了良知的孩子他会把道德当做自我需要,是我需要这个道德,不是用道德来束缚我。这篇小小的童话,我想之所以被教育部审定选中,就是这个原因。孩子到了小学三年级,他的眼睛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是他的内心生发各种欲望的时候,所以把这篇课文摆在小学三年级语文上册,很有道理,我也很高兴,整个初衷就是这样的。
Q:您参与创办《蜜蜂报》,能简单地介绍一下办报的宗旨吗?
辛勤:1980年,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了,我在呈贡县当了7年的小学老师和中学老师,又在县委会干了13年,这个时候有一个机会,让我来到了云南人民出版社担任编辑,来创办这张云南省少先队的队报。起名《蜜蜂报》,是因为蜜蜂很辛勤,我恰好叫辛勤,辛勤办《蜜蜂报》。初衷是希望我们的小读者像蜜蜂一样辛勤地劳动,也希望我自己像蜜蜂一样辛勤地酿蜜。蜜蜂是了不得的东西,没有人约束它,长大之后就自觉劳动,而且愉快地劳动,当一只蜜蜂感觉到自己快要死了,最后采了一次花粉,感觉不能把花粉运到巢里去的时候,它情愿掉头,飞到其他地方落下来,悄悄地死掉。没有哪只蜜蜂会飞回窝巢去死掉,因为一个蜂巢约有三万多只蜜蜂,每天都会有三百多只蜜蜂死掉,如果大家都飞回来,就增加别的蜜蜂的负担。
这种小小的昆虫有这种自觉性。自觉地劳动,愉快地劳动,当自己不能劳动的时候就坦然地消失,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精神。我创办这张报纸,就是要提倡蜜蜂的这种精神。当然,小昆虫的本性倒不是想着要为他人服务,但它的劳动在利己的时候也利他,所以我认为一个人利己不可怕,只是利己的同时也要利他,如果利己更他,那就更好。因此,我就把这张报纸定名为《蜜蜂报》。这张报纸在20年的时间里,专门有一个板块登儿童文学,培养了许多小作者,我经常会碰到一些当年的小读者,有的已经步入中年,他们见到我都会说,辛老师,我们是读着你的报纸长大的,“蜜蜂”两个字我们一直记着。
Q:“太阳鸟作家群”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文学现象,您作为太阳鸟作家群的作家之一,从个人角度来看,这个群体是怎样形成的?有哪些被忽视的情况?
辛勤:云南的儿童文学作家从起步时期,相处就很融洽。当时,在全国有影响的大概是那么几位,第一位普飞,农民作家,作品很多;第二位叫乔传藻,他是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初中就开始发表作品;第三位是钟宽洪,发表作品也很早。我则是1956年念初中的时候开始在《边疆文艺》(现《边疆文学》)发表作品的,接下来就是吴然、沈石溪、张祖渠、吴天、还有大理的张焰铎。
大家聚在一起,都非常地无私。谈到自己的创作构想,别人都会提意见,出点子。谁的作品发表了,有了收获,大家都很高兴。
这群作家里,有一位叫聂索,是聂耳的侄子,还有一位叫马瑞麟,一位叫康复昆,专门写儿童诗,这么一波儿童作家,搞了一次儿童文学征文,获奖那天下雪,颁奖是在中华小学。当时,有人就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儿童文学就像一个火塘,有火塘就有伙伴。”
关于太阳鸟,乔传藻老师写过一篇散文就叫《太阳鸟》,他觉得太阳鸟是一种群居的鸟类,色彩斑斓,一旦飞过山去就像一条彩虹。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曾在云南办过三位作家的作品讨论会,分别是沈石溪、吴然和我。我1984年发表过一篇中篇小说,刊登的杂志叫《巨人》,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发表之后又出了单行本,就叫《摔跤王》,1984 年获了上海的陈伯吹儿童文学年奖,那是云南省的作家第一次获上海的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当时,北京的《儿童文学》,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等都非常关注云南的这些作家。中少社就给我出版了一本书叫《鬼谷》,上海给我出版了四本,这是连续出版的小说其中两本书进入了少年文库。太阳鸟作家群最大的优点就是像太阳鸟鸟群一样的,各有各的色彩,各自又相互映衬,形成一条彩虹。后来,湘女陈约红老师和一些其他女作家, 她们应该算是紧跟上来的一群,成绩就更优秀,所以太阳鸟作家群是接着往前走的,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太阳鸟作家群有少数民族的作家参与,这么一个群体最大的长处就是,大家有一种使命感,因为云南神奇美丽丰富,儿童文学也应该神奇美丽丰富,所以云南作家的作品在省外的报刊杂志获得发表都是因为这一群人神奇美丽丰富。
Q:文学具有教化功能,良好的儿童教育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您认为当下的儿童教育最需要的是什么?
辛勤:一个孩子,一旦有了文学的修养,他即使变坏也不会野蛮,也不会残忍,也不会惨无人道。一个孩子早早的有了文学的修养,他的人性、品质,就要纯净得多,纯厚得多,纯善得多。儿童文学作品,具有这样的使命,唤醒孩子的良知,让他守住自己的良心,终身健康地成长。儿童教育相当的复杂,现在我认为我们教育最大的问题是,说的太大,起点不清楚,终点很辉煌,而起点明确是要靠儿童文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