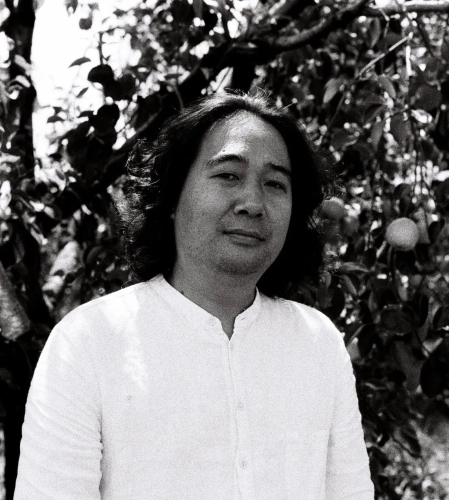编者按
2022年6月,第十届“云南文化精品工程”奖评选结果揭晓,昆明作家湘女儿童文学《好想长成一棵树》和马瑞翎长篇小说《独龙江上的小学》获奖。
此前5月底,《长江文艺》双年奖公布获奖结果,昆明作家包倬短篇小说《驯猴记》获奖。
此次获奖之前,湘女《好想长成一棵树》于2021年8月获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是本届获奖的唯一散文作品。马瑞翎《独龙江上的小学》于2020年4月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出版,之后3次加印,印量达4万册,入选中宣部2020年“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中文传媒十大好书等,签署了波兰文、意大利文2个文种版权输出协议,入选2020年度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包倬《驯猴记》在《长江文艺》2020年第10期发表后,被《小说选刊》2020年第11期、《新华文摘》2020年第24期先后转载。
获奖的三位昆明作家,湘女原名陈约红,曾为昆明市文联《滇池》杂志编辑,曾任昆明市文联儿童文学研究会会长;马瑞翎供职于云南某国企,现为昆明市文联儿童文学研究会理事;包倬现为昆明市文联《滇池》杂志主编、昆明作家协会副主席。在代际上,三位昆明作家分别属于50后、70后、80后。他们此次获奖,是昆明文学创作的又一重大收获。
近日,《昆明文艺》对昆明作家湘女、马瑞翎、包倬进行了访谈。
湘女:作家最可贵的精神是坚持
K
您长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散文《好想长成一棵树》2021年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份喜悦无疑包含着太多东西,比如,对儿童文学持久的爱以及不懈的创造,等等,借此机会,请您与我们分享一下。
湘女:我的儿童文学创作始于2000年。在这之前我写散文、小说,发表了不少作品,也出版了几本书。之所以转向儿童文学,得益于吴然老师。
吴然老师是全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也是云南儿童文学的标杆。他对我的写作一直很关注,也仔细分析过我的作品。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我的散文自然、优美、质朴、真实。这些都是儿童文学所具备的重要要素。而我的生活、我的性格、我的文笔以及他对我的了解,都更适合于儿童文学创作,他一直耐心地鼓励着我,希望我朝儿童文学努力。
正是有了他的鼓励,有了之前的写作积淀,我由成人作家向儿童文学创作的过渡就很自然。正如吴然老师所说,我过去所有的写作,其实都是在为儿童文学做准备。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充分的“准备”,我从2000年开始发表儿童文学作品,一直到今天,仍然在坚持。这期间,出版了多部儿童散文集和儿童小说,也获过不少奖项。
2021年,我的散文集《好想长成一棵树》获得了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个奖项,凝聚着吴然老师的心血,寄托着昆明儿研会多年的期待。是对我的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我们云南儿童文学作家的巨大鼓舞。
我觉得,一个写作者最可贵的精神,就是坚持,只有永远怀着对文学的虔诚与热爱,不离不弃,坚持下去,才能做好自己喜欢的事,有机会赢得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而我的坚持,有一个足够牢固的支撑点。
我在云南红河地区长大。我的儿童文学创作,就是从这里出发,以云南自然风光,少数民族文化为主题,展现云南的自然之美和民族文化之美,展示这片土地的丰厚情怀和少年儿童风貌。
云南独特的自然环境,丰富的民族风情,多元的边地文化,纷繁的历史烟云……太多奇诡绚丽,太多山水长情,太多充盈在天地间的自然神谕,地上地下,宝藏无数,等待着你去发现,去探索,去诠释,去创造……
《好想长成一棵树》,正是出于这种从小就被镌刻在灵魂里的云南情结,以树的形象,表达了我的自然心态、生命意识和写作情怀。
这就是支撑着我一路走来,勤奋创作的底气。可以说,儿童文学延续了我的文学梦,为我拓展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写作空间,打开了一个更为深远的文学视窗。
吴然老师说过,一个作家的创作,总是和他个人的经历、性格、气质、心理和修养等密切相关。对于我来说,我的写作浸透了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带有民族的地域的特色。
K
您曾是《滇池》杂志编辑,发现、培养过不少文学新人,我本人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就是您编辑发表的。文学杂志编辑和个人创作两者之间可能会有冲突,也可能会有促进,您是如何处理编辑和创作关系的,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湘女:很高兴徐兴正还记得我,也很高兴我曾经有过那么难忘的工作经历。当然,最高兴的是,因为这份经历,我结识了很多作者和文学爱好者,拥有了好多作家朋友,是文学让我们走到了一起,也是文学让我们维系了这样珍贵的友谊。
作为一名文学编辑,从走上这个岗位,我始终都投入最大的热情,诚挚地对待每一位作者,认真对待每一份来稿,也非常用心地呵护着我们的《滇池》,为她的纯粹与文采做过不懈的努力。
我对写作者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我敬重每一位作者和他的作品。我认为一个人能够对文学有如此痴情、如此执着,能够在各种艰难曲折中,追求自己的文学之梦,这本身就值得尊重,值得珍惜。我也走过与每一位作者相似的路,在写作上,有过坎坷,有过惊喜,有过发奋,有过失落……他们身上,有我的影子,他们的作品,很容易在我心里引起共鸣。
我觉得,文学编辑与个人创作并不冲突。每一次阅稿和编辑的过程,对我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我对他人作品做出评判的时候,实际也是对自己创作的一个审视,通过看到别人的长处,找到自己的不足,这样,对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高和启发。
我希望每一位文学编辑,都慎重对待每一份来稿,一定不要放过任何一点闪光,因为那是一个作者的心血与希望,如同一团微暗的火,会燃烧,会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K
您是云南太阳鸟作家群成员,这个群体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文学现象,与其他文学现象一样,外界的观察不一定完全到位。因此,请您介绍一下云南太阳鸟作家群可能被忽视的一些情况。
湘女: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云南的吴然、沈石溪、乔传藻、张昆华、辛勤、康复昆、普飞、汪叶菊、吴天等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作家名家,以他们丰富的、充满少数民族边地风情气息的儿童文学作品惊艳亮相,一举而成为享誉全国的云南太阳鸟作家群,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
这之后,随着云南儿童文学作家队伍的变化,太阳鸟作家群进入一个缓和期,创作态势趋于平稳,前行步履放慢。
2002年11月,我的儿童散文《竹娃娃》《喊月亮》在《儿童文学》杂志头条佳作栏目刊出。作品发表后,我在第一时间就收到吴然老师的信,信上说:“小陈你好!读了你发在第11期《儿童文学》上的两篇散文,高兴之至,欣喜之至,向你祝贺!这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美最动人的儿童散文佳作。它出自云南,出自你柔弱而坚韧之手,并非偶然。虽不是绝对必然,也是理所当然。这块芬芳的土地养育了你,你没有辜负她的养育。你的散文将使儿童文学界惊喜的目光再次投向云南……”
我理解吴然老师的喜悦,这些年来他一直在为太阳鸟的集结奋发而努力,一篇出自云南本土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尽管那么微不足道,却让他看到了一抹阳光。
这是太阳鸟重新振翅的信号。
在吴然老师给我的信里,包含着一个充满希望和期待的预言,那就是要放飞一群太阳鸟,让云南的儿童文学,走出云南,重新引起外界的关注,重新得到更多的重视,重新闪耀出云南之光。
自此,以湘女、杨保中、汤萍、余雷、蒋蓓、刘珈辰、沈涛、陈惠安、曾艳萍等为代表的云南儿童文学作家,在老作家们的鼎力支持、引导下,逐渐汇聚、壮大、成熟。他们的作品,延续着太阳鸟的风格,保持着鲜明的云南特色,充满对自然与人性的思考,在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作品中独具一格,不断冲向全国各个儿童文学刊物,各大出版社。云南的儿童文学作家,正在成为全国儿童文学创作的一支重要力量,得到全国文学界、评论界、出版界的关注和重视。
全国最权威的儿童文学刊物《儿童文学》,几次专程到云南召集太阳鸟作家们座谈、组稿,并推出云南作品专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的目光更高远,就是要把太阳鸟作家们的创作重心从单纯的儿童文学延伸到生态文学,延伸到当今世界共同关注的“保护生态、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地球家园”这一关乎人类生存的重大主题,为此,他们协同昆明儿研会,在昆明滇源镇建立起全国第一家儿童文学生态文学创作基地。
这样的提升,使儿童文学创作面更广,天更阔,内涵更丰富,意义更重大。
北京十月出版集团《十月少年文学》,也与太阳鸟作家建立起稳定的联系,多次刊发云南作家作品,并多次组织全国学生,利用假期,到云南与太阳鸟作家座谈,开展研学、阅读活动。
云南晨光出版社,更是对太阳鸟作家群呵护有加,大力推荐本土作家作品。
更重要的是,儿研会还得到了云南省作协、昆明市文联的大力支持和扶持。云南省作协为儿童文学作家们多次举办全国性的儿童文学研讨会,多次邀请国内名师大家举办讲座,指导、鼓励、支持云南儿童文学创作。同时,昆明市文联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为儿童文学作家创造条件,全身心投入写作。
此外,中国作协也为云南儿童文学作家给予了大力扶持,几位作家的童书都被列为国家重点出版图书项目。
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外界对云南儿童文学的重视和支持。而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我觉得有可能被外界忽略的是,云南太阳鸟作家群,是一个难得的老中青少汇聚的作家群体,这其中,有一对一的“拜师”指导,有新老作家的双重组合,有以点带面的创作交流,更有从不间断的对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形势的分析研究,深入探讨,寻找契合点……
今天,太阳鸟已经成为云南儿童文学作家特定的符号与标识,自带光芒,对明天充满了希望。
K
您曾任昆明儿童文学研究会会长,期间做了大量工作。回望过去,展望未来,您一定有不少感触和期待,请您谈谈全国视野下的昆明儿童文学创作。
湘女:昆明儿童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88年。到我参与这个协会工作时,儿研会已经是一个基础扎实、设置完善、运转规范的儿童文学创作中心,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我在儿研会先后担任了秘书长、副会长、会长、名誉会长……就我的工作经历而言,我觉得,正是基于这样良好的基础和实力,有了一代代太阳鸟们创建的丰硕成就、积累的丰富经验、所做的非凡努力,让后来者有了一个宽松的文学平台,营造了一种浓郁、专注的文学氛围,使大家能够脚踏实地,保持童心,潜心创作。
这些年,云南儿童文学从作家队伍到作品数量、质量都有了一次次的突破,云南儿童文学作家队伍不断加强作家队伍建设,发现新人,重点培养,加大扶持力度,鼓励多出精品,形成更强的冲击力。优秀作品屡屡登上全国权威儿童文学刊物,获奖连连。各少儿出版社也频频推出云南儿童文学作家重磅童书,引发一次次云南作品热。
但我们也看到,这些年来,正是儿童文学繁茂的黄金时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发展迅猛,很多省份已经形成了很强势的儿童文学创作群体,如江苏、辽宁、湖南、湖北、广西等更是儿童文学大省,每年涌现的优秀作家、优秀作品和全国获奖作品数不胜数。
相比之下,与全国儿童文学总体水平相比,云南还有着很大的差距,云南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水平和作品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云南有着很优秀,功底扎实的儿童文学老作家、也有着思维活跃、创作勤奋的中青年作家,但还需要有所突破,需要加强作家队伍建设,需要形成更强大的冲击力。
马瑞翎:作品要表现人类共通的情感
K
总体看来,您的创作庞杂丰富。长篇小说《独龙江上的小学》在这个谱系中处于一个什么坐标位置?对您的创作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马瑞翎:的确有点庞杂。2002年,我进入怒江工作。随后的几年,我坐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值班室里,心无旁骛地做学问、写文章。完全游离于文坛之外,处于一种边缘化的、个体独立的、纯属个人心灵自由的写作。此阶段的成果为中短篇小说集《最后的乐园》。这部集子收录了《最后的乐园》《达普洛的神仙》《三道溜索》《野人寨》等十余个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虽不甚成熟,但风格初现,自由奔放,令我欣喜。
大约在2008年左右,我进入“圈子”,开始参与文学活动,发表作品。此后的几年,是我自认为的创作黄金期。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我拥有一种对作家来说十分宝贵的东西:思想独悟与精神漫游。我总能够从司空见惯的平常景象中找到非凡的美的意象,发现那些微妙的、隐藏的东西。此阶段的代表作为63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怒江往事》和学术散文集《原始的终极地——怒苏部落》。
2014年至今,这应该算是转型期。我从当初的历史、文化类题材创作,逐步向现实主义转化。我希望自己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仍能保持独特的基因,能够形成一个自成风格的生态复合体,形成自身独特的语境。我为此而殚精竭虑。我自认为,此阶段的探索还是比较成功的。《独龙江上的小学》作为我的第一个实验性文本,既被视为主旋律性质很强烈的“主题书”,又被欧洲国家(意大利、波兰)引进版权。另一部佤族儿童题材小说《木鼓敲响的日子》,迄今为止已签署4份版权输出协议(波兰、埃及、蒙古、俄罗斯)。这至少说明,作品表现出了人类共通的情感,符合各国读者的认知规律。
《独龙江上的小学》的影响力比我的其他作品大。迄今为止已经获得二十余项荣誉。它是我在文学大山上攀登多年所找到的一个风景点。我在此看到了从前没有看到的一些东西。但我绝不会在此流连,而是会选择另一个方向继续前进。今后还会到达什么样的地方、邂逅什么样的风景,我对此充满期待与想象。
K
这部作品带有明确的地域标识和强烈的时代意识,您是如何产生创作念头的?它的构思和完成,是否有过曲折的经历?
马瑞翎:2016年我写过一个小短篇,写一位小学生过溜索去上学的故事。当时就想将它扩成一个长篇。这念头像一颗种子,保存在脑袋瓜里,一直没有拿出来播种。2018年我特别想逃离城市,希望自己像梭罗那样独自前往森林,在某个隐秘的地方待两年,把生活中的一切不属于文学的内容剔除干净,把生活过到最基本的形式。但事实上肉身是没法逃离的,唯有精神能够插上翅膀。所以,《独龙江上的小学》实际上是我在2018—2019年间精神漫游的成果。我写这个作品,没有什么曲折经历。那时我身在城市,心却去往担当力卡山。一些袖珍学校像上帝遗落的珍珠,零星散布在青山之中。孩子们每天清晨带着干粮,穿林过花、爬坡越涧到达老师身边。上午十点钟开始上课,下午四点钟放学……我以我的文学形式,还原着那艰苦而又美好的岁月,再现那个奇妙有趣的人文场景。
而现实中的“一师一校”现象,已经成为追忆。早在2010年左右,随着国家“集中办学”政策的实施,孩子们都被集中到“大”学校去住宿和学习去了,老师的头上也不用再戴很多帽子,独自干校长、副校长、年级组长、班主任、校医、理发师、炊事员和事务长。这部作品成了一扇温暖的记忆之窗。
Q
近些年,您的工作和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离开怒江到了昆明。这次在昆明写独龙江和以往在怒江写怒江,存在什么不同呢?
马瑞翎:对我来说,实际上“在昆明写独龙江”和“在怒江写怒江”没什么区别。因为我个人的精神早已转移到真正意义上的怒江少数民族的空间里去了。无论肉身处于什么样的地理位置,都不会给我的创作带来什么影响。我的位置很奇怪——既是写作对象中的一员,又永远成不了他们。总之我绝不会陷入“地域性写作”的困境。一个作家与他自身的知识储备、生活储备的关系,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当他打开仓库,感到自己与仓储的关系,不是一种相互捆绑的关系,而是一种亲切自然的重逢。
K
还是谈谈故乡这个话题吧。有人在故乡眺望诗和远方,也有人在他乡寻找故乡。您如何看待昆明这座城市,它是不是文学意义上的故乡?在这里,可以怎样安放自己?
马瑞翎:昆明是个神奇的地方。有时候我穿着薄薄的裙子,会在上班途中遇见有人穿羽绒服(连下巴都缩进衣领里);有时候我穿着长外套去上班,受到穿短袖体恤衫的同事的调侃。总之这是一个季节模糊的城市。它比季节界限分明的城市有趣。我像一只寄居蟹,自己把自己安放在这座城市的一套商品房里,时不时回忆年少时代。年少时代的故乡,小河潺潺、土地广阔、气候炎热、物产富饶。田野里哪个季节该长什么庄稼、荒地上哪个时候该开什么花,都是大自然说了算。偶尔有哪朵花不安分,提前几天亮相;哪个果子有了什么想法,要自己做主提前成熟,也不影响大局。优秀的本地狗们悠闲地在大路上、在村庄中行走,想躺在哪儿晒太阳就躺在哪儿晒太阳。它们在河床上打仗,在色彩缤纷的田野中奔驰、恋爱、结婚,在草堆里生下后代,而后被一位厉害的媳妇或者一位老实的媳妇,从中捉出一只,抱回家中去养,演绎一串关于生活的故事……
但现实中的故乡已经面目全非。野花们已经失踪。田野不再湿润水灵。空中刮过的风异常干燥,好像划一根火柴就可以点燃。商贩出售的水果,不仅在时令上乱了套,味道也同小时候吃过的水果不是一码事。狗也降级换代,全换成了小型犬,其血统乱七八糟,看上去很平庸,很不理想。优点是爱叫和吃得少。昔日的性格刚烈的本地狗,它们那惊天动地的吠叫声已经成为永远的绝唱。
我是否可以说:文学意义上的故乡其实已经消逝。它像去世的亲人那样,以另一种方式活着。它永存于回忆之中。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在意念中秒回。但人的肉身是永远回不到那里去了。
包倬:好小说打通个体与公众之间的
秘密通道
K
时代经验和世界想象都是大话题,它们可以用来谈小说吗?我认为,您的《驯猴记》很可能就是时代经验和世界想象的化解。对于这部短篇小说,你能否透露更多的秘密?
包倬:通常,我们会认为,时代经验是小说绕不开的话题。人(作家和人物),都是时代的产物。有人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有人被时代的巨浪裹挟,甚至被拍死在了沙滩上。“以某个时代为背景”,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话。但是,我认为好的写作是跨时代的。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的初衷肯定不仅是要刻画他那个时代。时代是个壳,装的是人心、人性、人类永恒的难题。时代是个背景,背景只是衬托。关于时代,狄更斯讲得更清楚,“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他要说什么?我的理解,就是对时代的化解。他告诉我们:任何时代都一样,充满了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也暗合了小说的复杂性。
关于世界想象。想象是对现实的补充。现实是个笼子。每一只笼中鸟都需要一双想象的翅膀。人类有想象力,才能活下去。否则,所见即现实,这人生也太悲催了。可是,想象也有局限性,它来自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我想,文学的功能之一是以想象力去探索世界。对我来说,每一次对想象力的调度,都是一次振翅高飞。我想飞得高一点、远一点,试图发现更宽广的世界。在这一次又一次奋力高飞中,将耗尽写作者的一生。
《驯猴记》写过三稿,三个结局。我写了三篇小说,以“记”为题,它们是《驯猴记》《走壁记》《掩耳记》,三个小说的人物是一样的,但是每篇小说中又各有侧重。三篇小说均指向一种未知的“宿命”,我以我的方式做着对世界的探索。
K
我预测,《驯猴记》将开启你中短篇小说创作新的可能。新就新在超越“经验”,可能上升为“寓言”。您如何看待这种可能?
包倬:我理解的写作,就是肉身的升腾。现实也好,经验也罢,它们既帮助了写作,也限制了写作。如果小说仅仅停留在经验阶段,那么不过是个体生命的呈现而已。小说是个体经验和公众心灵之间的隐秘通道。换句话说,小说需要普世价值。如果没有,就是一种猎奇式的写作。而在今天,这样的写作正在快速失效。
而寓言呢,是我们共同的命运。卡夫卡说,“一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我想,这个笼子就是寓言,是命运。不是鸟非得要进入笼子,而是笼子在寻找鸟。这是多么强大的威慑。纸上的文字看得见,而小说指向的是看不见。看不见,但又无处不在,这是文学意义之一种。
K
相对于散文而言,您在小说创作中,对现实素材的调度,总是更节省,也更大胆,似乎有“一个人就是千军万马”的孤注和孤勇。如果这是一种自觉的话,您肯定有不少考量吧?
包倬:首先,不管任何体裁,都是写人。而这个人,首先是作者自己。“我手写我心”,至今依然不过时。眼下有太多无“我”的写作。无“我”,就是为写作而写作。作为文学编辑,我经常碰到那种技术一流、语言一流,但读完却无法让人记住的作品。我为此而惋惜。在写作上,我是个笨拙的人,从不迷信自己的才华。我的理解是:写作从现实里来,到内心里去。海纳百川,而人心比海深。这才是文学千百年来吸引一代又一代作家投身其中的重要原因。
而现实素材是有限的,特别是对于散文,有些素材写完就完了。所以,我格外珍惜我的现实素材,再丰富的阅历也经不起浪费。而且,这种浪费会让文本变得滞重。现实素材就像味精,你不能把一整包味精一口气吃下去。我试着朝一个方向努力:用极少量的味精,烹制出一道好菜。好作品有文学意味。文学意味若隐若现,是捕风,是捉影。
只有对现实素材足够节省,我们的写作才能真的持续下去。而且需要在阅读和写作中,不断地唤醒记忆,为过去的时光招魂。
K
《滇池》在外界享有较高声誉,“北有《美文》,南有《滇池》”。陕西西安的《美文》是一本散文杂志,云南昆明的《滇池》是一本综合文学杂志,都是各自的城市名片。作为《滇池》主编,您和编辑部继承这份文学杂志“作家办刊”传统、推陈出新,将会进行哪些方面的尝试、探索和努力?
包倬:是的,文学杂志是城市名片。文学杂志的存在本身就很文学。文学对我们重要吗?在今天,从现实角度出发,它似乎并不影响衣食住行。可是人并不仅仅是需要吃饱穿暖。尼采说,人是动物和神之间的媒介。我们一生都在为此挣扎。而文学,让人彰显神性,而远离动物性。今天的现实世界里,越发荒诞,我想这和人们疏离、远离了文学有关。想想吧,一个人人只求现实利益的世界,那是多么可怕。所以,我甚至可以说,文学杂志是一个城市的尊严。有了文学杂志,并且高度尊崇文学杂志,我们才可以对外宣称这是一个有文化、有情怀、有精神向度的城市,而不仅仅是有高楼、有汽车、有商场。
《滇池》能有今天的影响力,确实得益于“作家办刊”的传统。老一代编辑米思及、著名诗人,红土诗派代表性人物;后来的主编张庆国,著名作家、云南省作协副主席;在《滇池》工作过,并对《滇池》的发展有着卓越贡献的雷平阳,是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云南省作协副主席。而我本人,成就远远不及前述诸位,但也在文学和办刊道路上孜孜以求。毫无疑问,“作家办刊”是个了不起的传统。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写作的人,才是最懂文学的人。就像你去菜市场买菜,最懂菜的人,不是菜贩子,不是买菜的人,而是菜农。
《滇池》从创刊之日起,就坚持着“不唯名家,不薄新人”的原则。四十三年来,我们参与了中国文学的进程。我们立足云南,但从来不是一个地方性杂志,而是在全国有着广泛影响力。一代又一代写作者,从《滇池》出发,取得了非常高的文学成就。远的不说,就我们身边,著名诗人于坚、作家胡性能、诗人艾泥等人的处女作,都发表在《滇池》杂志上。我想,这是编辑的眼光,也是《滇池》的荣光。
至于未来,我们的办刊宗旨不会变。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团结作家、鼓励新人。事实上,作家有长幼之分,但文学没有。我们只认好作品。我们坚守着文学的底线,拥抱那些热爱写作的人。而这份温暖和拥抱,是善和美的传递,必将感染更多的人。文章千古事。写作是马拉松,办刊也是,是一代一代人的坚守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