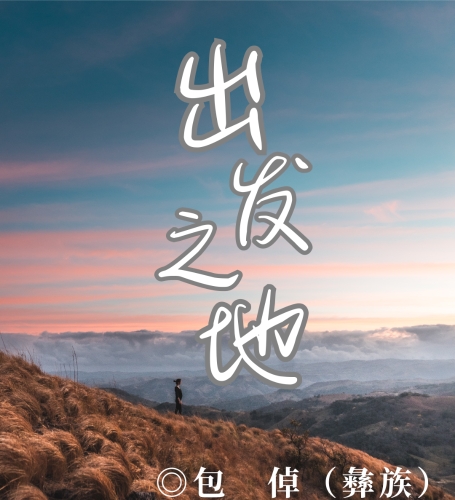包倬,彝族,1980 年生于四川凉山。《滇池》 文学杂志主编,昆明作协副主席。有小说和散文见《人民文学》《十月》《民族文学》《北京文学》等刊。出版有小说集《沉默》《十寻》《路边的西西弗斯》等。小说集《十寻》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我出生在这里。这个事实像看定的婚期,不可更改。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天大地大,我只能以一个弹丸之地作故乡。
这地方叫阿尼卡,地图上有。在西南方,如果你不懂一个地名是什么意思,那就猜它是来源于某种少数民族语言。阿尼卡,正是彝语“我要”之意。我要,是人面对天地万物最原始的表达。我们的一生都走在“我要”的路上。向天空要日月星辰,向群山要飞禽走兽,向土地要粮食蔬菜、孩子和马匹。
阿尼卡,一个被森林包围的村庄,绿色波涛的中心。地上长着玉米、土豆、红薯、花生、烟草,林间藏着杜仲、黄连、金银花、何首乌和接骨木。乔木是华山松和水冬瓜,而灌木庞杂,我们几乎叫不出名字。人与兽,世代为邻,但并非井水不犯河水。想想吧,那些斜挂在火塘边土墙上的猎枪,如果长时间不用,枪管会生锈;还有,那些牛背上的馋嘴小孩,如果条件允许,他们能够吃下一头活牛;对于野猪来说,地里的庄稼比野草美味;而圈里的母鸡,是狐狸的最爱。
大人们像一只只土拨鼠,手脚不停地向土地刨食。即使做梦,也是关于劳作。勤劳,是因为他们尝过贫穷的滋味。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大多来自天尽头。这不是夸张,而是肉眼所见。天尽头是药山,属于昭通巧家县,是古堂狼山的主峰。“朱提县西南二百里,有堂狼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飞鸟过之不能去。”(《华阳国志·南中志》)药山和阿尼卡之间,隔着金沙江。夏天雨后,金沙江上空架着一道彩虹。但连我这样的三岁小孩也知道,踏上那彩虹桥并不能抵达药山,而是会跌入金沙江里喂大鱼。那时的中国乡村,古老又年轻。一些伤筋动骨的往事翻了篇,剩下的就是过好自己的日子。披星戴月,背着太阳过山冈。除了双手,人们别无其他。要种地,要砍柴,要割草,要做饭,还要留出一只眼睛照看土地上爬行或奔跑的孩子们。能吃人的野兽没有了,但人比野兽更危险。特别是那些大雁一般总在秋天光临的货郎、不分季节现身的骡马贩子、神秘莫测的风水先生以及那些据说死后会变猫天天吃肉的媒婆……他们来自异乡,像童话里的巫婆,极有可能在某个瞬间转身就变成了人贩子。
这是两省三县的交界地。所谓三川半,其实就是偏僻的边角。我们住在会东县的地盘上,赶宁南县的集,娶巧家县的媳妇。会东是个新词,诞生于1952年。而在更久远的过去,比如清雍正六年(1728年),会东的大部分地区属位于西昌的宁远府管辖,而金沙江沿岸则属于云南的东川府。我的祖上自东川瓦泥寨跨江迁入凉山,如今看来,他们走得并不算远。1811年后的一百年,阿尼卡一带属于巧家厅。而另一端呢,是会理州。会东,会理的东边是也。这是一块拼凑出来的地盘。像一个男人娶亲之后,兄弟几个出钱出力,帮他成家立户。
史书浮光掠影,并以此证明人和村庄在历史长河中的渺小。可村庄对人来说,就是整个世界。站在村口,看见和想到的地方,统统属于未来。遥远让人生出抵达之心,无非时间迟早而已。即使是在只能靠双腿行走的年代,阿尼卡也不是绝对的孤岛。那些让我们父母提心吊胆的异乡人,操着奇怪的口音,带着各种洋玩意儿来到这大山深处的“马孔多”。我爷爷那个天才般的骡马贩子,和所有异乡人一见如故,让我家成了他们的免费客栈。大概从那时开始,就注定了我颠沛流离的未来。
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新街区新龙乡新桥村,我在三岁时就记住的地址。如果我不幸走丢或被人拐走,至少能够说清自己家住何方。我长到十三岁,去县城上学,每月向这个地址寄信,安抚我那含辛茹苦的父母。再后来,那个长着一张马脸的邮递员退休了,他和他的工作都进了时代博物馆。自1992年开始,大规模的人离乡背井,从阿尼卡或者会东去向更远的地方。一些地名被风从地图上吹起,晃晃悠悠,醉汉一般灌进群山的耳朵里。就连那些吉普赛人般的货郎也没了踪迹。渐渐地,不再需要通信了,可故乡的地址一直在。这就像我们身体里不经意留下的刺,久而久之,成了肉的一部分。
人挪活,树挪死,这是永恒的真理。人,就是大地上可以挪动的零件。正是这种挪动,让世界运转起来。挪动,就是来和去,是离开和回来,是从一个人的故乡到另一个人的故乡。个人的挪动是离乡,群体的挪动叫迁徙。摩西率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是挪动,湖广填四川是挪动,彝族人的六祖分支也是挪动。没有人是天生的土著,因为大地能让人存活,但本身并不出产人类。这里属于凉山,但彝族人口仅占8%不到。在这一带,汉族文化与彝族文化如河流汇合在一起,淙淙向前。
群山皱褶里的人们,唱金江小调或跳嘎且且撒勒舞得行,但谈起各家的来源都含糊不清。家谱上的白纸黑字,毁于水火,退化到了口口相传。若无文字,一切都变得可疑。比如我家在进入凉山之前,到底在哪里生活,就是一个无解之谜。
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在吃饱穿暖之前,根本没有“我要到哪里去”重要。因为所有的故乡都是出发之地。“一代人来,一代人去,大地永存,太阳照常升起。”这句话里藏着大地永存的秘密,那就是人类在地上的活动。没有人迹的世界,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要有光啊。活生生的人类是世界之光。
降生于世,如墨落白纸,命运之笔自有其书写之道。而生命本身,便是一个渐渐洇开的过程。洇,向外散开也。人在大地上的散开,足以书写一部交通史。起初,是双脚,然后,是马车,再后来,是自行车、汽车、高铁、飞机……至于未来还有什么交通工具,我们暂不知道。
八岁那年,我从阿尼卡走路去乡政府隔壁上小学。翻过山冈,蹚过河流,世界在脚步声中一点点扩大。原来这世界除了牛羊,还有书本。书本里有个大世界,书本也是通向大世界的道路。原来除了我们兄妹,这世界还有其他小孩。他们有的聪明,四清六活;有的笨拙,榆木疙瘩。每一间教室里,装着几十种未知的命运,像一个即将被打开的盲盒。野孩子们求学,如一群小鸟在练习飞翔,至于能飞多远,大概也只有天知道。
住在阿尼卡这种地方,就是住在井里。偶有飞机掠过天空,那轰隆之声仿佛天上有三盘石磨同时在转动。孩子们闻声而动,循声在地上奔跑。有人看见了,用手指着,目送那玩具般大小的飞机进入云层。前些年,云南冒出一支融合了原生态和摇滚的乐队叫山人,他们有句歌词:大白飞机擦天擦天呢飞。我们都懂,那是共同的记忆。
嘲笑一只井底之蛙,实属不该。如果有可能,谁不想做雄鹰?君不见,那些小青蛙趴在井壁四脚并用,努力向上,只为看到比井口更大的蓝天。而我们呢,嚼碎仅有的课本,只为翻山越岭,走进某种交通工具的肚子,奔向更远的地方。
——要像胥印侯那样成为传说。他出生的金沙江岸,距离阿尼卡仅有几十公里远。民间称他为胥六老爷,是个高大的胖子。他从金沙江岸出发,去了更远的地方,行商,参军,变卖家产,组建了会东历史上的第一支革命队伍——金江支队。若干年后,我去金江支队打响第一枪的地方看过,那是在会东境内的石家垭口。一条独路像把刀一样插进山里,风声呼啸,乱石嶙峋。确实,是上好的埋伏之地。
也正是因为有胥印侯,让会东县境内的很多地方,有了历史的印迹。比如雀衣坪子、大桥、江西街、堵格、鲹鱼河……这些随意而取的地名,被写进地方史,在历史和现实的交互中,回声隆隆。
印象中,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县城地摊上买过地方史小册子,里面有金江支队的记忆。胥印侯的后人那时和我一样,在县城求学。那时的会东,朴实如我们的父母,衣衫破旧。群山之中的“白色火柴盒”,还没被人称为金边银角或川滇明珠。
1993年的会东县民族中学像个土豆收购站。我们这些从群山里钻出来的少年就是个头稍大的土豆。那些个小的土豆留在乡村,繁衍生息,而我们这些幸运儿被暂时移植到了鲹鱼河畔。横滩桥下河水浑浊,少年们吐出青春的唾沫,以此测试水和桥之间的距离。汽车是稀罕之物,偶尔驶过,其目的似乎就是为了吸引路人的目光。自行车常见,是县城公职人员的交通工具,总将一只黑色小皮包挂在车把上。骑车者戴眼镜,穿着干净,脸上表情沉稳自信,是我们眼前活生生的楷模。
那时的会东也是个少年。一个建县四十余年的县城,正值青春期。熬过了童年的饥瘦,满心向往外面的世界。在遥远的南海边,有位老人画了一个圈。有人受到黑白电视的蛊惑,真的坐上汽车和火车去了外面,带回来的礼物中,必定有一只印着“深圳”二字的小皮包。
三十年了,会东县城的地图还印在我的脑海里。进入县城的公路有三条,分别是酒厂、丫口和小河嘴。从酒厂往下是丝厂,穿横滩桥至鲹鱼中学,过水厂,到广播电视大楼。多元公司是糖厂的,亮闪闪的建筑。灯光球场在体委,每年举行一次公判大会。我在那里听过惊悚的谋财害命和情杀,也遇见过一名做了小偷的小学同学。某次审判一个杀人犯,在押上囚车那一刻,他大叫“冤枉”,挣扎起来,掉了一只胶鞋。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冤枉,但那只死了主人的鞋子久久留在原地,无人敢碰。文化馆门口经常站着杂耍艺人和猴子。他们当众表演咽喉顶钢筋和空袋生蛋。在艺人表演的时候,那聪明的猴子端着盘子来求打赏。但过不了多久,艺人开始驯猴,那猴子又免不了因为不配合而被打。文化馆里有录像厅,镭射屏幕,座位很软,票价和旁边的硬座录像厅一样。电子游戏室里打斗声震天响,玩的是街霸或者三国志,一块钱三个游戏币,永远除不尽余数。那是县城少年们出入的场所,像我这种农村孩子,往往避而远之。我至今未学会任何电子游戏,想必就是那时候形成的心理屏障。百货公司是周末必去的,当然只能看看。明亮的玻璃柜台里,盛放着少年们的梦。柜台后面的售货员烫着大波浪,涂了红唇,满身香气但脾气暴躁。她们也是少年的梦——长大后要娶一个这样的女人。还有什么呢?庄重的大礼堂,是入团宣誓之地。对面餐馆里的鸡火丝香飘十里。斜对面是老邮电局,我在那里寄出第一封去向阿尼卡的信。再往上,就是老县委。直属小学在营盘山,那里有发表过作文的小学生。农贸街是热闹之地。对馋学生来说,在街口的豆花饭店花十块钱买一碗米饭、二两卤肉、一个白菜豆腐汤,便能吃得腹鼓如蛙。而如果是在学校食堂,十块钱是两天的生活费。街道两边的铁棚里,摆着或挂着批发自成都荷花池或昆明螺蛳湾的衣服和裤子。当然,这两个地方不产衣物,它们应该是来自更远的广东。据说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间是论斤买卖,但这丝毫不影响这些衣物在我们心里的地位。它们鲜艳、时尚,若能从牙缝里省钱买下一件,乡村少年立马就有了城里人的模样。这条街上的风里都带着钱的味道。已经有点改革开放的样子了。生意人操着异乡口音,舌灿如莲,叫价和成交价之间相差十万八千里,而我们这些少年往往因为不敢还价而吃亏。大概是1994年左右,县城里有了开发区。一夜之间,菜地上建起了楼房,那是宾馆和住宅,产权属于矿山。这么一对比,那些红砖房和水泥外墙的房子就显得落寞,被弃之日不远也。烟草产业正在兴起,我的父母也是烟农。我在县城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拜阿尼卡所赐。它们来自山上的树木、圈里的猪仔和地里的烟草。会东县东西南北四方距离七八十公里,气候和出产两重天。距离阿尼卡不远的大崇一带在金沙江边,是最早的富庶之地。出产甘蔗和蚕丝,而高寒的野租一带,彝族世居,那里几乎只出产土豆、玉米和燕麦。野租即原来的会理七甲半夷区,属于凉山比较纯正的彝族聚居地。我的同学十有八九来自野租,只有极少部分像我这样的来自汉族地区,不会讲彝语,受尽欺负。此后几年,我混迹于街头,除了阅读不再学习,这大概和被欺负有关系。几十名同学来自会东各乡镇,他们就是流动的地方史。相比生养我们的村庄,县城已属异乡。总有一个时刻,我们会讲起各自的衣胞之地。我正是从同学的描述中,对会东的人文历史有了初印象。来自大崇的同学,自然是要讲到胥印侯的。那语气里有掩饰不住的骄傲。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因为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而产生了某种关联,这是大地之子的认同。少年的讲述来自民间传说,有几分经不住唯物主义的推敲。而传说,正是文学的启蒙。就像希腊神话中,宙斯和诸神是否真的存在一点都不重要,我们需要的是盗火的勇气。每个少年的心里都藏有一个普罗米修斯,讲述即是明证。来自者堡的同学岂肯示弱?胥印侯算什么?我们那里出过土司呢。土司,知道吧?不是外国人吃的那种,而是土皇帝,辖地能跑死马,杀人就像杀鸡。“者堡土司四个碉,四个都使银皮包。过路君子不识宝,沉香当作烂柴烧”。确实,这是我从小听过的故事。不光是故事,还有歌谣,我爷爷会唱。土司衙门遗址还在。残垣上盖了民房,里面住着人,基脚处有枪眼。门前的石狮子也在,嘴里含着绣球,手能伸进去,却无法将绣球掏出来。有史为证:从1710年至1932年,宁南、会东、会理一带,均是这禄氏土司的领地。而我们的祖先,要么是他的子民,要么是他的对手。那是群狼环伺的年代,土司、官府、地方势力,你死我活。二百多年来,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战争、背叛、爱情、传说,如果写下,就是一部《百年孤独》。自元代开始,西南方的历史里,就少不了土司。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土皇帝,鸦片、女人、枪炮、银子……贫民的梦中之物,他们触手可及。凉山历史上有四大土司,闻名遐迩,会东者堡禄氏土司,其实仅为土百户。可在被他统治的子民眼里则不一样了。一切都是宿命,是神的旨意。成败兴衰,皆是天道。而我们这些青涩少年哪懂这些?我们像一个个巨大的口袋,向这世界索求着食物和爱。我们永远感到饥饿,胃是填不饱的深渊。每次从餐馆前走过,该死的鼻子总能闻见饭菜香,喉咙变成了长江黄河,唾液汹涌。另外,我们还需要爱。关于爱情的小说和电影,已经不能满足我们那被施了肥的身体。必须要有一个人,在心里想着,远在天边或近在眼前。但对知识的渴求却未必。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求学是件多此一举的事。我们亲眼所见某个大字不识的人发了财,穿戴光鲜,被人簇拥着,像个港台明星。改革开放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一些观念悄然改变。比如长期因稳定而令人羡慕的教师,首先产生了自我怀疑。有位教师读了贾平凹的《废都》,在课堂上哀叹:九等人是教员,鱿鱼海参认不全。有个庞然大物,昏昏沉睡多年,如今醒来,迈开脚步向前进,地动山摇。我们,只不过是庞然大物身上的一根毛。被它带着,风驰电掣穿过河流山川,农村城市。世界是因人而存在,还是它本身一直在?比如那列载我离开凉山的火车,如果我不乘坐,不关注,不去想起,它是否依旧穿梭在莽莽群山中。眼见为实,眼不见为虚?我亲眼所见的是火车里装着成百上千个不安的灵魂,他们的未来只有天知道。所有人都行囊简单,想法天真,以为外面的世界金钱会像树叶般飘落。新千年来临,世界迷茫又冲动。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一次次希望和失望交替,昆明接纳了我。某天我突然发现,昆明距离会东也不过四百公里。而且无论从哪个方向走,都无法绕开金沙江。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离乡而未走远,我心安了。自此以后,会东是左胸前的衣兜。像当年县城文化馆门口的魔术师,我的衣兜看似空空如也,实则取之不尽。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在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里写:“对于作家来说,自己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我觉得他说的不够准确。对于作家来说,世界的中心是十八岁前居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你对世界的初印象,只比胎记晚一步。从童年到现在,再到未来,我们这一生仿佛都是在与时间抗争。而世界,只是我们的战场。童年我站在阿尼卡遥望药山,后来我身在昆明遥想阿尼卡。谈不上爱与恨,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习惯。这种习惯对一个写作者来说,体现在书架上。我的书架上有两格关于凉山历史以及彝族研究的书。以史为鉴,照亮的是过去和现在。像一束光穿过时间,让那些人和事成了玉玦。我成了一个寻找玉玦的人。关于胥印侯和他的金江支队,德昌籍作家马懋阳写过《金江风暴》,那是一个老人用脚丈量出来的文字。而关于者堡土司,我在出版于1874年的《会理州志》上读到:“者堡土司百户禄恩锡,其先禄阿格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投诚。雍正八年(1730)因乌东夷叛,其子日升出师有功,乾隆四年(1739)于请留土司呈开收等事议叙案内,准给百户职衔,颁给钤记、号纸,历传禄景曜、禄国辅承袭,住牧者堡。”史书上的寥寥数语像种子,一旦落到地上便活了,有血有肉,枝蔓丛生。二百多年的者堡土司史,太多散佚于风中。会东一带民间流传的,基本上是末代土司禄安佑的故事。那些故事充满了阴谋与背叛,神话与现实。口说无凭,见证者何人?丁文江是也。1914年的阿尼卡是什么样?书里没有记载。而距此五十公里的苦竹,此时已是活泼泼的人间。土司衙门在此,杀戮已经持续三月,草木皆兵。六月十八日下午,有人拿来官衔名片和云南都督府的护照求见。来人丁文江,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此一程,丁文江专为探矿而来。他从云南个旧到昆明,再到会理通安,接下来的目的地是云南东川。会理去东川,路有两条:一是原路返回昆明,再去东川;二是穿过会理东边(即现在的会东),跨过金沙江进入东川地界。其时土司府,执掌者为已逝土司禄绍武的太太方氏。方氏二十多岁,知书达理。即使是见多识广的丁文江,也在其文集中赞美她“是我生平所见东方人中少见的美人”。一个科学家和一个女土司在民国三年相遇,并不是为了演绎一场惊世之恋,而是科学家要过会理东边的彝区,来求女土司派人护送。丁文江在苦竹土司府住了一晚。在《丁文江文集》第七卷中,对土司衙门和方氏有如下描述:“村子四围有土筑的城墙,墙上站着有拿枪的士兵。但是我并没有受任何的盘诘就一直走到衙门前面。老差人指着对我道:‘委员,你看这座衙门,多么阔绰。房子都是砌在山上;从大门到后门,一共九进,一进比一进高。听说是仿照七重金鸾殿砌的!’我抬头一看,果然是一个绝大的衙门,比会理县署雄壮得多。”“看见一位二十多岁的妇人,前后十几个差役簇拥着,迎将出来……头上盘着青色的‘锣锅帽’,身上着一件青布的大袖长袄,下边束着百褶裙子;身材在五尺一寸左右,一双天足,鹅蛋式的脸,雪白皮肤;眉毛虽不是很细,却是弯长;眼睛虽不是很大,却是椭圆;鼻梁虽不很高,却是端正;嘴虽不是很小,嘴唇却是很薄很红。”丁文江此行,有个重大的遗憾——他未能给方太太拍照。他要求了,但被拒绝,理由是“现在大太太自氏死了才三个月,尚在服中,照像恐不便。”所以,只能通过丁文江的文字让民国年间的土司得以显影。这是一次各取所需的相遇。科学家求护送,女土司求捎信给大总统。原来这万人之上的女土司当得也不顺心。改土归流声势浩大,西南各方土司势力纷纷瓦解。丈夫禄绍武因受命征讨染疾而亡,大太太自氏被杀害,振兴土司家业的重任落在了年轻的方氏身上。她写了一封信,请丁文江带去北京。信中简述了禄氏土司源起、对边疆安定的劳苦功高,以及自己所受的屈辱。总之一句话:请大总统允许她继续世袭土司之职。丁文江在文章的结尾,照录了方氏给大总统的信。信用古文写就,文辞飞扬,超乎人们对一个彝族土司太太的想象。由此可见,那时汉文化对彝族上层人士的影响。1914年6月,总统还是孙中山。而等丁文江于民国四年(1915年)回到北京,呈上方氏之信,那时的总统已经是袁世凯了。此信“被部里的长官原呈发还,说不是本部所管,不必多事。”时代风云变幻,深居大凉山深处的女土司未必知道。托人稍信上路,像是将一颗种子埋进土里,发什么芽,开什么花,岂是她能左右。丁文江呈信未果,心怀牵念,1915年夏天,“通安土州有人来说会理县长又与苦竹土司冲突,已经请兵去进攻。”又因披砂(即今宁南)已经设了新县,遂感叹“恐怕方太太就是尚在人间也不能再做女土皇帝了”。但丁文江没有想到,锲而不舍的方太太曾在1916年获任四川将军委任的夷务宣抚官,如愿以偿。可那真是土司的黄昏了。
……
(阅读全文,请见《民族文学》汉文版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