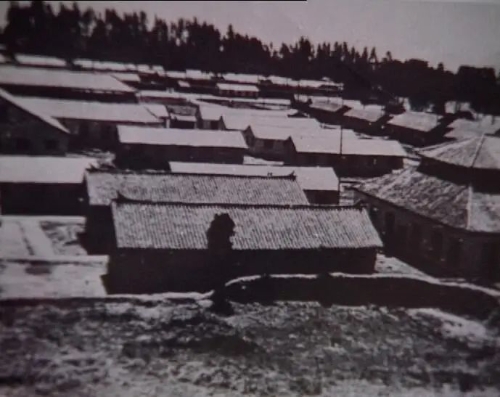在清华园,杨振宁有一番从容的回忆:昆明,大家知道是四季如春的地方。我在那边度过了七年。对于昆明,我觉得等于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们刚刚到昆明的时候,对于昆明有个特别好的印象……当时以前的云南的钱——纸币,叫作“老滇票”。定的十比一,跟重庆的法币。因为我们拿的是法币,拿来买昆明的东西变得非常之便宜。
其实它应称为“新滇币”。当年龙云请缪云台回云南重振富滇银行,发行“新滇币”,使云南财政相对独立。在最初联大人的口中,“老滇票”引申出一个贬义,它比法币的币值低,被用来代指“昆明人”,意思是“老土”。
首先征服北方人的是云南可爱的气候。
哲学系女生郑敏说:昆明的气候是很慈善——老天爷是很慈悲的,冬天只要一件毛衣或者一个薄棉袄就能过了。当时我们都是很穷的,我记得好像都没有袜子穿,也就这么过来了。但是,在那个生活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穷苦的感觉。
东北流亡学生李晓深有感触:我们当时在云南很穷,我就有一件毛衣。冬天的时候,有钱的同学把棉袍借给我穿,当时我们的茅草棚窗子都没有,就是几根木头。要不是那个气候能够只穿一件毛衣,否则不可能生活下去。
王力太太夏蔚霞说:我在昆明住得非常高兴,因为昆明实在是好地方。
我为什么怀念昆明?昆明天气好,物价便宜。我们刚去的时候用的是滇币,老滇币一块抵十块。后来又变新滇币,一块抵五块。
我们住在农村,什么东西都是吃新鲜的。后来有很多东西我都是从昆明学会的,做咸菜,昆明的茄子鲊、韭菜花、干巴菌。干巴菌最好吃了,我非常怀念。昆明的米线,我认为焖鸡米线比过桥米线好吃。后来我们再去昆明的时候,我不好意思自己出去吃焖鸡米线。他们开他们的会,我就偷偷地一个人出去吃。还有一种普通老百姓常常吃的烧饵块,圆圆的。粤秀中学的学生来上课以前,就吃门口的烧饵块,我觉得那有什么好吃?后来吃吃看,真的是好吃。抹上辣椒酱,真好吃。螺蛳米线、腌菜、大头菜,大头菜我喜欢空口吃,因为不咸。在我们住的地方的底下有一个包子铺,卖一种破酥包,特别好吃。我现在还非常怀念那个破酥包。所以,我对昆明特别有感情。
为学校选择昆明为目的地,是蒋梦麟校长之功:
在这样的气候之下,自然是花卉遍地,瓜果满园。甜瓜、茄子和香橼都大得出奇。老百姓不必怎么辛勤工作,就可以谋生糊口,因此他们的生活非常悠闲自得。初从沿海省份来的人,常常会为当地居民慢吞吞的样子而生气,但是这些生客不久之后也就被悠闲的风气同化了。(《西潮》)
闻一多的女儿闻铭回忆悠然时光:
在晋宁的时候,我父亲休假。正好他准备开“上古文学史”的课,有时候,他备课间隙,就带着我们出去。在晋宁郊外,有草地,有田,他带上一块毯子,往草地上一铺,再泡上一壶茶。他跟我母亲就坐在那儿,喝着茶。我们在旁边翻跟头,抓蝴蝶,在草地上玩儿。他和我母亲看着我们,笑眯眯的。
等我们玩得差不多了,他把我们叫过来,有时候给我们讲远古的神话,有时候教我们背唐诗。我们一边背唐诗,一边在野外的环境中玩儿。昆明的天特别蓝,又高又蓝,白云在上面飘,远处是一片绿。那时候虽然小,可是真觉得自己好像走到诗境里去了,这对我们的心灵也是一种陶冶。
另外,他也很喜欢在月夜里教我们背唐诗。在晋宁的时候,我们住在楼上,窗户很大。到了晚上,月亮升起来,把窗户打开,月光能散到整个屋里。在这个时候,在一片月光底下,他也教我们唐诗,让我们背,给我们讲。我记得《春江花月夜》就是这时学的,印象特别深。
崇尚“气节”的共鸣,使西南联大与昆明本土发生了精神血脉的深度交流与情感寄托。君子交于义,小人交于利。云南人民与联大人的情感,有一个最大的信念作为底盘,就是“家国情怀”。
父亲说,自从西南联大的名人教授来到昆明城,昆明的富家人就不好意思穿绫罗绸缎了,因为觉得国家都已经将亡了。这么多的名人都这样来到我们这里,如此俭朴地生活着,自己还摆什么阔气呢。太太小姐们纷纷收起那些讲究的衣服,穿起蓝布衫走进学堂。山城中那种狭小的夸豪斗富的风气为之一改。
费孝通说,昆明生活对于他个人,是很值得留恋的一段历史,是这块土地成就了他:
这一段历史,我觉得(是)值得纪念的。这段历史里边,我认识了主要的一个问题。我在研究农村,写了一部(书),现在已经写成英文的,叫Earth Bound China,翻译出来是《束缚在土地上的中国》。那时(工业)还没有发展,云南农村还是(处在)旧的传统的经济之下的。这本书后来一直到1987年才翻译成中文,叫作《云南三村》。我的主要学术上的成就在云南这一段,以这本书(为代表)了,就是《云南三村》,内地三村,云南三个村子,在滇池旁边。
前几年我也去了一趟(云南),去看一看旧的地方。云南风景美丽气候很好,是值得我留恋的地方。同时我接触了云南的很多乡亲,接触他们,(在)生活方面了解他们,觉得很亲热。我常常想念他们。
费孝通在战时的考察研究中,提出“乡土中国”的理念。其价值并不在乎是否成熟完整,而是一个方向,鼓舞和支持着来自象牙塔内的人们,去发现自己本土的文化和资源,有“振奋士气”之功。云南所具备的丰富的社会历史与自然资源,正可以作为“乡土中国”的一个缩影。
1938年,西南联大接到教育部的文件,奉命协助云南开办师范学院:
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是1938年遵教育部命令增设的。当时在全国共增设师范学院6所,除西南联大外,中央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临时大学(后改名西北联合大学)同时增设,在湖南蓝田单独建立一所,称为国立师范学院。为了加强对师范教育的领导,教育部同时颁布了《师范教育规程》,对培养目标、入学资格、学习年限乃至院长的聘任等等,都做出具体规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院系史》)
师院学生修习课程虽与其他学院的学生一起上课,而要求标准不同:
作为未来中学教师的师院学生所需要的知识结构,与文、理学院各学系学生不尽相同,即便是同一名称的课程,其深度、广度、重点也不完全一样,因此师范学院在发展过程中,针对师范教育的特殊性曾独立开出一些专业必修课程,以适应师院学生学习的需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院系史》)
从此,云南的中学师资教育得到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升学率大为上升。
对于昆明市民而言,影响最广泛和轰动的是联大教授们的社会演讲。当时很多是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办,状若盛典。我父亲说,店铺到下午都把门板上起来了,因为老板和伙计都要去听先生们讲课。
我看到当年由云南政府印的一本小册子,上面是这类“社会讲课”的内容,有梁思成的建筑学、潘光旦的优生学、吴晗的历史学,刘文典讲《庄子》。这些当代中国最前卫的学问,就这样向着昆明幸运的市民们开放了。我父亲那时已在银行就职,听这些演讲成为他这样的职业青年学习的机会。
据何炳棣先生在《读书阅世六十年》中回忆:
1944年春间在联大新校舍遇到闻先生,他问我的近况,我告诉他为解决住的问题,我在大西门外昆华中学兼课已半年多,虽只一间,宿舍楼固窗明,条件还可以。他说住在乡下本来是为躲避日机轰炸,往返二十余里很不方便,如果昆华中学能供给两间房子,他可以考虑去兼课。我立即把闻先生的意愿告诉李埏(云大文史系讲师,兼任昆中教务主任),他和徐天祥校长喜出望外,立即决定以原医务室的小楼楼上全部划为闻先生全家住处。我记得楼转弯处的平台还不算小,可以煮饭烧菜囤放松枝。楼外空旷,住定了后,闻师母开辟了小菜园,颇不乏田园风趣。
这种直接介入当地学校教育的举动很快蔚然成风,来自中国最高端和最开放地区的文化输入与教育熏陶,在西南联大落户云南的七年中,迅速地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
天祥中学成为名家荟萃的中学,王力在粤秀中学任教,还为这所中学写了校歌。
我母亲在昆明市女中读书,她们的老师是联大学子,东北流亡青年。那个年代的昆明中学生,每天耳濡目染的都是“联大文化”。由于大批联大学生家庭在沦陷区,断绝了经济供给,还有很多人到云南的专县上去当中学老师。
学子郑道津,后来留任云南个旧一中的校长,他总结道:
联大到了昆明之后,由于联大的学生往往没有经济来源,生活无着,不得不到校外工作。昆明的就业范围是有限的。但随着抗日战争这个大形势的振动,各个地方势力也感觉需要人才,才能赶上形势。抗战不久,各个地方办教育的形式也大大小小地多了起来。有些地方大力发展教育,办的中学能扩展到一些小的县份。在这种情况下,联大学生为了解决自己求学的需要,相当多的人开始下乡,就成为县城和城镇中学老师队伍中的重要力量。
这些人到了地方,开始使云南的教育在教学的深度上大大改进。
随后每座县城至少都有一所中学,有条件的还有一所高中,学生就能到昆明来考大学了。联大后期云南籍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是很大的。地方教育马上就打开一种新的局面了。
【作者简介】
张曼菱,籍贯云南华宁。1978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82年在《当代》《收获》发表中篇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云》。同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改编拍摄为电影《青春祭》。2003年4月主持西南联大纪录片项目《西南联大启示录》,在央视十频道《探索·发现》热播,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散文集《中国布衣》《北大回忆》等。